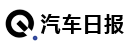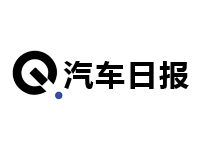几十年的套娃脸重要换了,大众颜值担当Arteon
之前网上盛传一个段子:“一交警路口查超速,向局里汇报:“刚才有辆帕萨特超速50%,哦,好像是迈腾,不对,速腾,哦,我再观察下,又好像是朗逸,怎么又有点像新捷达……报告领导,刚才一辆大众车超速50%。”
什么?
你觉得是这个交警不行
那好
我把大众所有车拉出来
你要能全说对
mini请你吃榴莲
怎么样
是不是一脸懵逼 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大众就一会这样,我的答案是不,最近又来了一辆。
8月份的大众之夜上,全新五门GT车型Arteon第一次亮相他将会是大众CC的换代车型。我们先来欣赏一波图。。
它拥有优雅的设计元素,四门轿跑车的运动感,以及宽阔的闲置空间。采用不同于大众其他汽车风格的前脸,并且拥有较长的轴距,桥跑似的溜背设计,以及更大的掀背式尾门。横条幅格栅与灯组内的LED光源相连,视觉效果使得前脸更加舒展,同时新车还将配备有全LED大灯组。
大众Arteon内饰设计追求上以简洁为主,整体大众家族化的内饰设计风格,其中贯穿式空调出风口是车内设计亮点,大尺寸中控屏幕,木纹试装饰板和中央时钟提升豪华质感。三幅式真皮多功能方向盘采用平底设计,目的准求更多运动感。
作为未来大众CC的继承者,大众Arteon采用无边框车窗设计,对于GT车型来说,设计非常动感。
大众Arteon在漂亮的外观下依然有着很好的实用性,比Passat更长的轴距让它有着充足的乘坐空间,在后备箱空间很大的同时还采用了掀背开启的尾门。很显然,大众是汲取了CC的教训,希望Arteon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买单。这台最大功率达到280Ps的2.0T发动机的实际表现完全对得起它的账面数据,0-100km/h加速只需要5.6秒,性能表现完全不需要怀疑。不过R-Line版本的20寸轮毂导致这台车开起来的舒适感有所欠缺,即便是在舒适模式下,来自路面的细碎震动还是很明显,再配合R-Line更加偏向于运动性的悬挂,始终给人一种紧绷的感觉。
最后想要讨论的是Arteon的中文名,车透君想到的是“昂腾”,谐音、意思以及在大众车系中的用词定位都挺搭,有媒体老湿想到的是“雅腾”,从优雅度上也挺搭。等到新车国产亮相时,又会有何惊喜呢?
台湾日据时期“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始末析
内容提要日据时期的“治警事件”促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被称为“台湾政治史上的里程碑”。本研究对大量一手史料以及新旧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立足这一事件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如何互动,来研究“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台湾民众唯一言论机关《台湾民报》发挥资讯传递、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功能与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进行舆论较量;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治警事件”被捕者互相呼应,汇成共同力量。台湾民族运动人士所使用的舆论抗争武器,主要来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祖国反帝民族运动的思想方法以及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启蒙。“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凸显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成为中国现代史中反帝、反侵略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台湾;日据时期;治警事件;舆论抗争
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抗日运动一般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作为分界,前期是武力反抗日本统治的时期,后期则是进入非武装政治运动阶段。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运动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西来庵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经法院定谳处死的起义群众达866人,武装抗日失败惨痛的教训使台湾民众特别是中上层人士认识到无法靠传统落后的武力和以现代化装备起来的日本军队硬碰硬;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思潮日渐向世界各地蔓延,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朝鲜的独立运动等如火如荼地进行,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时期,民本主义蔚为思想主流,台湾殖民地政府自后藤新平以来亦试图以怀柔治台;这些都促使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其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由武力转变为采用文化启蒙与政治运动的各种非武装的抗争方式。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1921年起到1934年止,历时十四年,期间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十五回请愿,是日据时期最大、历时最久的非武装政治运动,意图突破总督府的专制统治,寻求在台湾建立具有特别立法权与预算权的议会。它是台湾民众试图突破殖民地统治的困局而发起一项自发性努力,在内涵上具有典型的以启蒙思想与争取政治权利为主旨的近代式政治运动的特征。
1921年和1922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在台湾引起巨大的震撼。1922年8月,台湾总督府对请愿运动正式开始采取对策,请愿运动一时受到打击。为此,大多数请愿运动参与者认为有进行政治结社的必要。蔡培火与蒋渭水等人决定成立以促进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为直接目标的团体——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于1923年1月16日,向台北市北警察署提出结社报备。1922年2月2日,台湾总督府以妨害安宁秩序为名,根据治安警察法禁止该社。蔡培火、蒋渭水等人转而向东京早稻田警察署申请结社,获准,1923年2月21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正式成立。1923年12月16日,台湾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全岛同步逮捕、搜索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达99人,这是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第一次大规模逮捕非武装抗日知识分子,史称“治警事件”,即“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在东京被认为合法的结社,在台湾则被视为违法,体现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法域的不同,政治味之浓烈,自不待言。
台北地方检察官长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理由,对蒋渭水等十八人予以起诉。第一审宣告被告全部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第二审除其中五人无罪外,其余十三人被判罪(禁锢七人,罚金六人),被告不服上诉,第三审被驳回维持原判决。
“治警事件”是日据时期首例“政治案件”,促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将反对总督府专制的政治运动推到最高点,被称为“台湾政治史上的里程碑”,“台湾十年社会运动史的第一座山峰”。“治警事件”亦被认为在台湾新闻及报纸发展历史上,影响最大。
目前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史的文献都有提到“治警事件”,但专门对其进行研究还相当匮乏,且已有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治警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台湾蒋朝根编著的《狮子狩与狮子吼:治警事件90周年纪念专刊》、台湾高日文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台湾苏恒钦的《治警事件探讨》、大陆焦萍的《“治警事件”:日据时期首例“政治案件”之研究》等。然而,为何“治警事件”能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台湾民众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民报》在这次舆论抗争中如何发挥作用?台湾民族运动者如何运用多种形式的舆论抗争,以唤醒民心,凝聚民气?“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有着什么样的互动?目前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缺乏研究。而厘清这些问题,可进一步认识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殖民统治抗争的实质,在当前蔡英文当局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历史,制造台独史观的背景下,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大量一手史料以及新旧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研究“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治警事件”起因及事件初期的信息封锁与反封锁
(一)台湾总督府发动“治警事件”的原因
“台湾议会请愿出现之时,台湾人的人格于焉诞生”。散处于各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知识分子,群集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旗帜之下,形成共同战线:在岛内以文化协会为中心,在日本以新民会、台湾青年会为核心;在祖国大陆,则由蔡惠如等与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留学生互通声息;从而形成台湾、东京、祖国大陆相互呼应之势,共同推进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在殖民地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是台湾总督府为了顺利地统治台湾民众而进行怀柔的主要对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让台湾总督府感到震惊的是其致力于怀柔的“本地资产阶级势力举起(叛)旗,与新兴知识阶级结合”。台湾总督府认为“本运动至少是迈向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一个阶段,而其运动将继续到获得完全的殖民地自治为止,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本运动被强调则民族意识将愈见旺盛,反抗气氛将愈见旺盛,反抗气氛将愈形浓厚。”因此,第一回请愿时,总督田健治郎就明确表示“台湾议会的设置,有违统治方针,如果强要,可谓叛逆”。
台湾总督府碍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是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虽然采用施压、取缔、个别劝令、离间分化等各种手段欲将之打压与消弭,终究未能如愿。1923年1月1日,台湾总督府将日本国内专门取缔思想运动的“治安警察法”引入台湾,为取缔台湾社会运动奠定法源基础,以便其对“民族自决的信心坚决”,且“急进的过激分子,严加取缔”。1923年2月2日,台湾总督府运用“治安警察法”禁止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结社,对于其在东京重新成立,总督府深为不满,暗中计划予以痛击,于1923年底制造“治警事件”,显示总督府对台湾民族运动,已由怀柔方针转向弹压方针。
(二)事件初期总督府的信息封锁
“治警事件”是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经过周密的计划与极度保密而发动的。事件发生后,一切对外交通、莫论(无论)电话、电信、除官方以外,私人的通信均被控制。街头巷尾以及公共场所,均有特务人员在监视。对于漏网的同志,也派有特务人员跟踪。台湾总督府将此事件界定为“台湾的内治独立阴谋团秘密结社”, 并对媒体下达两个半月的“新闻箝口令”。 “过了一个多月,三部报纸连载一字都没有”。事后,日本国内的《大阪每日新闻社》对此记述道“对今春以来进行中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关于这记事,不使写一行,偶然有内地新闻对于本事件的记事或论及到总督政治,总督官宪乃过于郑重,一一将那记事割去,绝对不欲使岛民得知事件的真相。”
台湾总督府处理“治警事件”的方式让全台湾被不安与恐怖的气氛所弥漫,“倾然全岛几为疑惑误解之空穴所包围,岛民之恐怖几乎达于极点。” 以为又要发生与西来庵事件同样性质的悲剧。
(三)信息突破和各界支援
为防止总督府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叶荣钟突破日本特务层层的跟踪,找到《朝日新闻》驻台湾的蒲田特派员,“我要求蒲田将事情转告该社政治部部长神田正雄,赶快将事件的详情报道出来”。同时,运用管道寄出三封信到东京“这三封信是事件发生后,东京方面的同志最初接到的情报。在东京的同志接到消息,马上开会讨论善后事宜,并向日本朝野呼吁,早日解除台湾总督府的封锁措施,结束黑暗的恐怖政治。一面蒲田特派员的通信,也由东京《朝日新闻》刊载出来,台湾总督府也只好不为已甚,台湾的社会,渐次恢复政策的状态,人心也就日趋安定了”。
对于《朝日新闻》的这个报道,以往的文献有提到过,但缺乏详细报道内容。笔者通过“朝日新闻缩印版(1897-1999)”数据库,查找到《朝日新闻》于1923年12月25日刊发的日文报道《台湾议会请愿运动 七十余名知识分子涉嫌违反治警法被逮捕》,这应该就是叶荣钟所提到的那个报道,其全文如下:
“本月16日上午6时在台湾全岛各地爆发的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其主谋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蔡式谷等以下70余人被逮捕。同时警方对其住宅进行了严格搜查。
被拘留者为:…….以上被捕者皆为台湾知识分子,其中十余名是医生,三名是律师。他们分别被关押在台北警察练习所和台中某学校。被捕理由是,他们不满治警法禁止结社的规定而发动了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违反了治警法。此案将于近期开庭公开审判。(台北电报)”
这篇报道在标题即以“知识分子”称呼“治警事件”被捕人士,并强调“以上被捕者皆为台湾知识分子,其中十余名是医生,三名是律师。”显示被捕人士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而且在《朝日新闻》所详细列举的被拘留者名单,有一大部分是受日本教育、具备近代教养,且说一口流利日语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日本政界、学界所熟知,很难被当作“土匪对待”。这篇报道让总督府的大检举曝光。
东京留学生从叶荣钟信中获知大检举的消息后。1924年1月5日,林呈禄等十六人集会,针对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被拘捕事件,决定唤起广泛的舆论,扩大向议会呼吁,具体的方法包括:访问新闻杂志社、招待记者、访问自由法曹团、策动议员在议会质询等,并决议各部门负责人。清濑一郎(简称清濑)、田川大吉郎(简称田川)两位议员在议会中提出《关于组织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事实质询主旨书》的书面质询,虽然因议会的解散未获结论,但也使“治警事件”引发日本本土关注。
由于《朝日新闻》最早发表“治警事件”报道、再加上平时同情台湾的日本中央政要、东京台籍留学生和祖国大陆声援的共同努力,“治警事件”引发台湾岛内外关注,突破总督府的信息封锁。台湾官宪在压力下,法庭审判过程才得以公开出来。
二、《台湾民报》与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的舆论较量
《台湾日日新报》是“日本官方在台最重要的言论工具。”1911年到1937年,《台湾日日新报》实行的是日文版添加两页汉文版面的作法。
《台湾民报》由东京留学生创办的《台湾青年》《台湾》发展而来,1923年4月15日创刊。在当时总督府在台湾实行创办发行报刊许可(批准)制,剥夺台湾人民自由创办发行报刊权利的背景下,《台湾民报》利用日本本土和台湾新闻管制程度的不同,在东京印刷,发行范围除了台湾,也在日本本岛及祖国大陆沿海流通。《台湾民报》以“创设民众的言论机关”为使命,其主干蒋渭水、林呈禄等十三人都在“治警事件”被告十八人当中,《台湾民报》因为主要干部被逮捕而于1924年1月号发刊后暂时停刊,直到2月复刊。
笔者通过关键词查询“《台湾民报》数据库”和“《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数据库,从1923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发生)到1925年12月31日关于“治警事件”的相关报道、评论。(1925年6月16日“治警事件”被捕者石焕长最后一个出狱。为查询相对完整,笔者将查询时间延长到1925年12月31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相关的报道、评论、读者来信等共58篇,其中37篇为日文版、21篇为中文版;《台湾民报》相关的报道、评论、狱中文学、读者来信等共117篇,并针对第一次公判和第二次公判发行两次公判号(第一次公判号页数26页,第二次公判号22页,都超过以往《台湾民报》平均发行16页左右的篇幅)。如表1所示。
新闻报道的书写方式决定了事件被人认识的内涵,作为台湾民众唯一言论机关的《台湾民报》与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对于“治警事件”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呈现,体现了台湾民族运动人士与总督府在“治警事件”上的舆论较量。
表1:《台湾民报》和《台湾日日新报》相关治警事件的报道、评论等
资料来源:笔者通过关键词查询“《台湾民报》数据库”和“《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数据库整理得出。
(一)第一次公判前的舆论抗争
《台湾日日新报》对“治警事件”的报道最早始于1924年3月2日,正是在这一天,台湾检察机构发布预审决定、总督府的“新闻箝口令”解除。这一天《台湾日日新报》发表4篇日文版报道和1篇中文版报道,分别是:日文版《策划本岛内治独立的十四名嫌疑人被起诉 治安警察法矛头直指 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秘密结社》(同样的内容中文版报道为《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预审终结》)日文版《到形成犯罪为止,同盟会成员的基本活动及其罪行》,这三篇主要从官方立场阐述起诉理由,而且中日文版联合刊登预审决定的主文和理由,目的是让懂日文和懂中文的读者都了解,以实现其威吓效果。日文版的《他们并非勇士 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跟风 三好检察官谈》《法律问题暂且不论 政治思想问题上的其实十分重要 长尾辩护律师谈》,通过访谈呼应官方观点。
1924年3月4日和3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分别发表《台湾议会与请愿运动(上) 民族自决主义与本岛的实情》和《台湾议会与请愿运动(下) 首先要慢慢成为有能力的国民》两篇日文版的评论,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界定为“不是一场正经的运动”,认为被检举的人是“表面上这样提一提,背地里却挑拨民族感情,煽动动乱倾向。……必须禁止,……法律必须发挥其威信。”并于1924年4月10日,在中文版刊登《一本岛民之告白》的所谓读者来信,夸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认为“治警事件”是某团体煽动学生引起的,“惟是对与头脑如白纸之学生。加以种种之煽动。不导之正。而诱之邪。”
《台湾民报》最早关于“治警事件”的信息来自1924年1月1日刊登的《贺来长官访问记》,通报“治警事件”日本官方的态度,其内容是“在东京的林呈禄访问贺来总务长官于东京,询问台湾此回关于0000000000之事件,长官答曰‘此回的事件是我来京后的事不尽明白,既是有检查官底调查、问题在乎司法权之手、现在还未得十分明白的报告了’”。根据上下文及当时新闻箝口令的背景推断,该报道中的“0000000000”应该指的是“治警事件”。这一期的社论《迎年词》,用“天将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来鼓舞民众,“大家要鼓舞新元气努力奋斗,才能达到人生光明的境地啦。”
1924年2月18日,台湾杂志社决定停刊日文的《台湾》杂志,全力经营《台湾民报》,使得《台湾民报》更加集中加强对“治警事件”的相关报道、评论。
对于以《台湾日日新报》为代表的御用报纸对被检举者的漫加批判,《台湾民报》反驳道“检举了数十位先觉者,然后其过了一个多月之间,三部报纸连载一字都没有,…。然后三月二日,检察局也发表其内容了。台湾报纸虽载得非常详细,然因未及公判,故不得预料其结果如何、且漫加批判,待看其了局罢!”
这一阶段正是日本大正民主时期,日本效法西欧,改行君主立宪,追求立宪、法治、民主、参与等价值,日本媒体对于台湾总督府制造“治警事件”也有不少批评。《台湾民报》及时进行翻译转载,借助来自日本国内的批判,凸显台湾总督府的冥顽不灵,亦是对御用报纸的有力回击,这一策略一直贯穿于整个“治警事件”始终。
《台湾民报》最早转载翻译的日本本土报道来自《大阪朝日新闻》1924年3月16日刊登的《台湾议会之起诉案件》,认为“台湾议会请愿设置运动,决不是对总督政府的叛逆者。”指责此次的检举是“无理态度,是不贤明的措施。”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转载翻译的《大阪每日新闻》社说《台湾的自治热》,强调“总督府如果信了依这样的检举,就能够绝减他们的特别议会设置运动,其误解就可谓太甚了。吾们看这回的做法,视为倒注油于该运动的。”
《台湾民报》还大量刊登“治警事件”主要被诉者在被拘留和服刑期间所创作的大量狱中作品。1924年2月21日刊登的第一篇入狱文学是蒋渭水于创作的《快入来辞 于台北监狱》,表述其“策士同以归正,共扶人道复奚疑”的心志。这些狱中文学展示被捕者服刑期间坚毅而淡定的心境,刻画出他们家国民族之大爱,营造了全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动员效果,反驳了《台湾日日新报》对被诉者的抹黑。
为了能在《台湾民报》上刊登,不被总督府政府禁止发行,这些狱中文学尽量写得能“通过”的尺寸,所以也就不写许多隐情。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些狱中文学被命令删减,或不得刊行。如蒋渭水的《狱中日记》系列在《台湾民报》的第2卷第12号未被台湾总督府允许刊出。蒋渭水的《送王君入狱序》一文,被总督府当做不稳删去,成为“断头断脚不具的东西。”
(二)第一次公判时的舆论抗争
“治警事件”第一次公判从1924年7月25日起至8月7日止,前后开过九次公判庭。
三好检查官的求刑论告前后长达六小时,被认为“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威吓宣传文。”通篇都在斥责被告等人反对内地延长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台湾日日新闻》对此分别刊登3篇日文版和1篇中文版的报道,以标题的形式评价检察官“总结发言字字达人肺腑 至诚至忠”,突出其对被告的斥责“被告只懂模仿甘地缺点之愚蠢 宣告不满现在的统治者请离开台湾”。
被告林幼春、林呈禄、陈逢源、蒋渭水与蔡培火作为代表进行法庭陈述。《台湾日日新报》对此刊登5篇日文报道,3篇中文报道。将被告定性为“策划台湾独立自治 轻举妄动的十八叛党”。描述被告“或翻预审之供述。或以官宪之报告为无实。或谓打电脱同盟会。……被告之陈述颇怪”。日文版的报道《治警法违反案宣判 被告陈述中均带有逃避责任的言语 废话连篇》《治警法违反案宣判 面对法官的质问,被告方陈述混乱,丑态百出》《治警法违反案宣判 蒋渭水因无视法庭之神圣 三好检察官要求其退廷(庭) 蒋渭水退缩》对被告进行贬低。
《台湾民报》作为旬刊,为弥补时效性较慢的缺点,于1924年9月1日发行公判号。其社论《正义与权力》由《台湾民报》专务理事、“治警事件”被诉者林呈禄执笔,写道“史上既无阻止时势得住之势力,自知正义必无不收最后之胜利”。显示被诉者无畏无惧的心境,鼓舞民心。
针对《台湾日日新报》对被告法庭陈述的贬低,《台湾民报》此次公判号,在导语上,即对被告的法庭答辩评述到“各被告对裁判长的答辩,皆是滔滔不竭语调鹰扬、言语明晰、真不愧志士的气概了。”
与《台湾日日新报》偏颇有选择的报道相比,公判号详细记载了整个公判过程,强调“以下全部是记者在公判庭见闻的”,采取的是客观报道的手法,而其原因在于“吾人不幸居在聋子、哑子之地位,又事属刑事问题,不敢多辩是非黑白。只将形成事实记之,惟望世人以公平、理智之眼光判断已而。”一审公判号用2.33页的篇幅记录三好检察官的论告,用10页多的篇幅记录辩护人的辩论,用8页多的篇幅记录被告的陈述,并用加括号形容三好检查官“声音极厉,颜色凄怆”;描述公判现场“无立锥的余地”。
对于三好检查官在论告中激动地说“既不喜欢同化政策,此际宜离开台湾。”《台湾民报》在公判号中,特别用“。。。。。”提醒读者注意,同时发表蒋渭水所写的《这句话非同小可!》的社论,指出1922年翻译简某说了“你大定若嫌税贵,尽可退去台湾罢”,被当局免职。“你是个堂堂的检查官长,敕任官,竟也敢说了这句话,那责任自然要加倍了。”对三好这句征服者口吻的殖民主义叫嚣进行严厉批判。
(三)第二次公判时的舆论抗争
第二审公判自1924年10月5日至10月29日,开庭3次。
对于此次的法庭辩论,《台湾日日新报》强调“面对伴野审判长针针见血的尖锐质问 被告均苦于辩解”;形容用三个半小时为被告辩护的律师清濑“通过提高音量来引起审判长注意 大显身手”。
《台湾民报》于1924年11月11日发行二审公判号,采用更多的字体变化、标记符号“…”、“。。。。。”来凸显内容,并将有利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言论放大处理。如对于林呈禄的供述,导语特意用大字号字体突出其供述重点“东京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完全存在 台湾议会请愿趣旨始终不变。”在《清濑博士的辩论》报道中,其导语写道“(清濑)为被告挥泪热辩激动听众、痛论帝国对殖民地的方针、释明台湾议会的请愿是正当的要求”,并用整段的大号字体来凸显清濑的主要观点。
对于第二次公判的结果,《台湾日日新报》以统治者的观点报道判决刑期——《治安警察法违反案件宣判有罪 首谋被判四个月监禁 次要嫌疑人监禁三个月并罚金百元 五人被判无罪》,描述“退庭的被告的悲哀;无罪的欢喜”。
《台湾民报》则在公判号《治警事件第二审判决》报道中,描述“被告等虽被宣言有罪、其态度如平日、莞尔告人曰是仅上告之必要”,凸显被告的从容不惊。该公判号的《正义追悼会》报道,记述了东京留学生的反应:“时莫不与兴奋昂腾,几乎涨满会场,众口皆曰、正义亡矣!”并在《编辑余话》发表评论,“夫欲谋我台人多人之幸福与权利者、于牺牲之一途所不能免也、倘有蒙何等之迫害、而被告等亦皆有深甚之觉悟也。”显示台湾民族运动人士深切感受到任何政治权利的争取与获得,都必须付出牺牲与代价。
针对御用报纸在第一次、第二次公判中的歪曲报道,《台湾民报》与之对抗的逻辑是揭露它们选择性地报道法庭辩论过程,立场不公允。如1925年1月1日刊登蒋渭水的评论《偏要饶舌什么?》,批驳御用报纸:“请你老实说来,那公判事件,对于检察官的论告和求刑之言,第一审和第二审就刊得半句一句都未漏掉,那辩护士和各被告的辩论、第一审没有刊出、第二审只刊出两三句。这可叫做公平吗?叫做完全刊出吗?……咳!‘牛面前弹琴’实在没有当用的。”
《台湾民报》还转载大阪每日新闻社、日本紫峰译神户区洛尼区留英文闻社、日报时报英字纸的等日本主流媒体的评论,来批判二审判决的不公,“台湾之高等法院因欲帮助时代错误之政策有辱司法独立之名声矣”。
(四)三审判决后的舆论斗争
这一阶段,《台湾民报》和《台湾日日新报》的交锋在“治警事件”善后的评论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5年2月20日,第三审判决结果出来:驳回上告,维持第二审的原判决。《台湾日日新报》于1925年2月24日发表日文版的《治警法违反案的善后 以及关于司法独立权问题》评论,站在总督府的立场批判“治警事件”被捕人员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此,《台湾民报》于1925年3月11日,发表评论《谬论纠正》,逐一对《台湾日日新报》评论中的观点进行批驳。
《台湾日日新报》针对“治警事件”声称“实在台湾于思想方面较朝鲜较为平稳无事。……今日弄出这样的结果,是吾人之所以为憾的”。《台湾民报》反驳到:“真的,我们也是很以为憾!不过你们的遗憾和我们的是不同其种类的。你们以为台湾人是可以任意压迫、任意剥夺,而台湾人又甘于奴隶生活、是奴隶模性的人类、所以不该有这样的行动要求自治、平等无差别——而近年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你们引以为憾罢!不然他们受了刑罚不是你们所额手相庆的吗?这还有什么遗憾!”凸显台湾民族意识的觉醒。
《台湾日日新报》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一方面假惺惺的表示“吾辈言论界中人,对于这种运动欲把持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却指责这是“将到底办不到的事情,籍请愿权之名来强请。”《台湾民报》直指这些御用文人的虚假和无知,批驳到“强请吗?能不能自然有法律来解决,如何能强请?我们读了这句可以判断这篇文的作者是没有常识的、像你这样头脑石化的人、虽欲把持充分理解也不能,故不但不声援,并且要极力妨害这种运动,这是必然的事。”
对于《台湾日日新闻》认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若强要做这件事,其结果必定要触着宪法,而犯帝国议会的权能”。《台湾民报》反驳到:“呵!你们的前提是‘强做’,然而在法治国下岂容强做?我们必不强做,必以法律从事。所以一定不会触着宪法,况堂堂的立法机关的帝国议会尚不敢认为违宪。试看这五六次的却下理由都是‘尚早’而非‘违宪’。‘尚早’是承认将来有许可之一日。你一个小小的新闻社何以敢说这是违宪?”有理有据的凸显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合法合宪的。
与之前反驳言论相比,这一次《台湾民报》言辞更加激烈,显示经过“治警事件”,《台湾民报》的作风愈加大胆。
(五)“治警事件”对《台湾民报》的影响
“治警事件”虽使台湾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物身陷牢狱之灾,却激起了民众关心政治的热潮,每次开庭都吸引了满堂关怀的民众。在法庭辩论上,检辩双方针对日本殖民地统治方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理由、有无违宪等政治主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对台湾民众亦是生动的政治教育。在这过程中,《台湾民报》发挥资讯传递、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让以往分散而弱势的民间抗日力量有了公开持久的信息发布平台,汇聚形成与官方舆论对抗的力量,促进民众的觉醒。“诸公一片献身社会之苦心,已足使吾同胞感激涕零,永铭肺腑矣……僕不才深愿附诸公之骥尾。”
尽管《台湾民报》的报道经常受到总督府干涉,如“本报前号的编辑余话,因说及这次的治警公判事件,招惹当局的忌讳,遂被割去一角。”但其公判号依旧收到读者热烈欢迎,“增印一万本之多通过后不费几日则行销完毕。”
经过“治警事件”的锻炼,《台湾民报》发展迅速,1925年的新年特刊,页数暴增至96页(平时发行16页),有64页广告,数百家商号刊登贺年广告。1925年7月12日,《台湾民报》改为周刊,读者群从1923年创刊初期的二千多人,增长到1925年8月26日的1万人,其发行量与同期台湾三大御用报纸相差无几,具有“登高而呼,四山皆应”的效果。正如因林呈禄入狱而继任《台湾民报》总编辑的谢春木所说的“由最高四个月的监禁,使四百万余同胞觉醒,……《台湾民报》得以急速发展,很快祝贺发行一万份。由此看来,这是一次非常廉价的宣传。这次事件是十年社会运动史的第一座山峰,越过了山峰,平原就自然地展现在面前了。”
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治警事件”被捕者的互相声援
“治警事件”是西来庵事件以来,台湾政治社会运动者第一次受到共同的迫害,台湾总督府处理“治警事件”的小题大做,使政治社会运动者变成英雄,“一狱成名”,强化民气。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报》被誉为日据时期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的三大主力,分别由外交、民间和宣传上做努力。“治警事件”中,民族运动人士不仅运用《台湾民报》与总督府进行舆论抗争,也积极通过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治警事件”被捕者互相声援,汇成共同的力量,将台湾当时的政治文化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治警事件”议题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议题互相交织呼应,使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被激发,为请愿运动凝聚更多民心。第五次请愿运动蒋渭水、蔡培火两位“未决囚”担任请愿委员赴东京请愿,在《请愿理由书》中附上《台湾官方对于请愿人的压迫》,特别提到“治警事件”:“拘禁者约五十名,检阅岛内通信,停止日台电报,使全岛化为黑暗世界….. 实对全岛有识阶级以未曾有的恐怖和激愤。兹观其事件之发端,因大正十二年(1923年)一月一日起,依据台湾同胞施行未赋予行政裁判救济制度之治安警察法。”此次请愿受到日本媒体、政界的瞩目,也进一步让日本国内了解“治警事件”真相。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台湾总督专门从台湾赶到日本,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蔡、蒋等人的非难不对。
由御用绅士组成的公益会干部在《台湾日日新报》社长井村大吉(时任总督府通信局长,是新任总督内田嘉吉的亲信)的斡旋下,于1924年6月27日举行“有力者大会”,宣称请愿运动是少数人“不满足于台湾文化现状,妄为空想所驱”的作为,指责蒋渭水、蔡培火为“破禁而触法者”。意图阻扰请愿运动,向新任内田嘉吉总督交心。对此,1924年7月3日林献堂亲自指挥,与“治警事件”被检举者林幼春、蔡惠如等人和其他民族运动人士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一起举行“全岛无力者大会”,发表《全岛无力者大会宣扬书》,决议:“吾人为维护吾人之自由与权利,期撲减诸如捏造舆论、蹂躏正义、自称全岛有力者大会之怪物。”“无力者大会”数千人参加,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挞伐,不但使“有力者大会”烟消云散,也台湾公益会无疾而终,有力的声援了请愿运动以及“治警事件”被诉者,振奋了人心,签署人数由第四次请愿的71名(当时“治警事件”刚发生,主要干部纷纷被捕)回升至第五次请愿的233人。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合法性得到了普遍确认,不再被随意指为违宪,也使更多台湾民众加入请愿队伍。第六次请愿人数增至782名(正值“治警事件”二审宣判结果出来,被告不服上诉之际,原本蛰伏的林献堂再次领导请愿运动),第七次请愿人数增长至1990人。(“治警事件”被捕出狱者蔡培火、陈逢源等担任此次请愿代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成为台湾民众籍以宣泄其民族情感的一股洪流。
“治警事件”也使得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渐趋高潮。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为宗旨,不仅在各地开设读报社,也开办各种讲习会、夏季学校、文化演讲、文化演剧等,其中演讲会是其最重视的活动。在当时的台湾,由于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民众的知识程度较低,文化协会以演讲会作为联结、动员群众的主要方法,用面对面口语传播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新思潮。演讲会最常利用的场地是各地的妈祖宫、天公庙、圣宫庙等广场,以及戏园、舞台或是公会堂等民众日常聚集使用的公共空间,便于人们共同交谈与行动,各种阶级与身份,得以自由进出往来,得到普通民众的热切参与。
“治警事件”发生后,台湾文化协会更积极的开展巡回演讲,如表2所示。讲演内容也更为尖锐,直接攻击总督府的专制统治,要求废除恶法、废除保甲制度、社会改造等。
表 2 1923年-1926年台湾文化协会演讲情况
资料来源: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台湾:晨星出版社,第351页。
“治警事件”18名被告皆是文化协会干部,他们的被检举激发民众去听演讲以为行动后援。“治警法违反嫌疑事件,因判决为有罪,一般民众大受其刺激,各地方致书来社(台北支局)、聘出张(出差)讲演,每日数通。”文化演讲带动了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另一种参与,民众也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交通不便的山地甚至抬轿迎送,用打鼓吹做先导,宛然如请妈祖的情形。”二审判决结果出来后,蒋渭水、王敏川、蔡惠如演讲时“听者三四百名皆不畏炎威烈日,过午后犹不忍散,至闭会始归,其热心之态度洵令人感佩焉。”
《台湾民报》亦及时报道评论请愿运动和文化协会的演讲,产生“扩散效应”,形成对“治警事件”被捕者有力的声援。总督府原本想通过“治警事件”压制民族运动,不但未达目的,反而唤起了民众的民族自觉,被捕的民族运动人士被视为“英雄偶像”,出狱时“各商家住家、一齐放起爆竹。”更重要的是,这些民族运动人士在精神上已克服了对官宪压力的恐惧,在出狱之后抗日作风更为大胆和积极,再加上民气高涨的配合,遂使抗日运动在治警事件后,进入一个普遍化、行动化、更广泛群众参与的新阶段。
四、“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与社会大环境的互动
(一)“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与一战后的民族自决思潮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殖民帝国、内部弱点纷纷暴露,为了得到殖民地的支持,往往以战后自治权相许,到了大战末期,各殖民地一致要求英、法等国实现诺言,反侵略、反帝国主义的呼声相继而起。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原则,其中的民族自决的主张更促成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民族自决运动风起云涌。这种思潮也强烈冲击着台湾民众的心灵,尤其是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学生,在敏锐的民族意识下,自然也深受这一世界性民族自决主义潮流的刺激。“凡具有新鲜的感触和思想活跃的人,对于这次的欧洲大战,必把他过去的信仰希望,起个新陈代谢……回顾我们的台湾,虽是海绝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难道无一点刺激?况且我们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积弱既久,兼之治于强权之下,凡有人类应享的自由幸福,都为一种高气压似的制度压下去,所以对这样世界的大变动,好像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示。”正是在这样“反抗的暗示”的鼓舞下,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对台湾政治改革的想法转为积极,要求自治的意识高涨,开展了各项民族运动。
“治警事件”中的亲历者蔡培火、叶荣钟等在其回忆中,都一再强调大战后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他们的影响。台湾民众在“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亦处处可见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影响。如《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里以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德国合并法属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俄罗斯同化乌克兰、英国统治爱尔兰等例子来说明高压手段实行同化政策的结果,小则引起反抗,大则刺激独立意志,稳健的自治统治政策方为可行之道。以先进国的殖民经验来否认日本在台湾实行同化政策的可行性。“治警事件”法庭辩论中,林呈禄指出,国际联盟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还未得自立的人民要图该人民的的福祉和发达,才是文明(国家)的神圣使命”,特别强调“日本是为世界的文明国家,因要提高其地位,须排斥这样非文明的专制政治不可。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统治的大精神,就是要达文明国的神圣使命。”像日本官宪这样因方便就采用内地延长主义,不方便之时就主张特别统治主义,这是不诚意的政治。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对向来的统治方针没有革新的打算,“就没有资格加入领有殖民地文明国家之列。” 其论述中强烈暗示,作为文明后进国的日本,应该以文明先进国为师,顺应一战后民族自治主义的国际潮流,才有资格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
由此可见,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将他们所吸收的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加以应用进行攻防,作为舆论斗争的有利武器,来检视日本的殖民主义,暴露日本在台湾统治的蛮横与虚伪本质,更显有理有据,翻转殖民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主被动地位。台湾民众所进行的包括“治警事件”在内的各项民族运动亦成为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运动的重要一环。
(二)“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与大正民主
一次大战后的日本国内正值政党政治、普选运动、民本主义声势大振的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日本走上实质上的近代型立宪君主制。大正民主虽然未能成熟到使日本摆脱军国主义思想,却也提供一定的养分,给予在日本留学的台湾知识分子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出现了一批同情台湾的日本知识分子,并迫使总督府在制造“治警事件”时失去武力镇压的正当性,从而为民族运动人士舆论抗争提供一定的空间。
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非武装抗日采取的是“间接牵制主义”行动模式,这主要来自1907年祖国政治家梁启超对林献堂的忠告,“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厚结日本中央显要,以牵制总督府对台胞的苛政,进而取得参政权以影响日人的政策,伺机达到回归祖国的目的。”1913年与孙中山同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的戴季陶亦对台湾民族运动领导人物提出类似的忠告。“治警事件”舆论斗争中,民族运动人士采用“间接牵制主义”行动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借用日本国内的主流论述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员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里,开篇就写道“谨按‘大日本帝国’立宪法治国”,来提出“设置台湾民选议会,付与施行台湾之特别法律及台湾预算之协赞权”。他们以立宪主义的三权分立原则作为设置台湾议会的重要理由之一,诉诸大正民主时期有关立宪政治、殖民地自治论、文明殖民论、人道主义等主流论述,行使的是宪法所赋予的请愿权,这使得总督府因强制使用“治安警察法”来制造“治警事件”陷入了理论上的被动和道德上的破产,为舆论抗争奠定基础。
其次,以夷(日本人)制夷(在台日人)的策略,诉诸日本本土朝野以博取同情,结交日本国内自由开明人士,以牵制总督府。如神田正雄最早在《朝日新闻》刊登“治警事件”消息;日本众议院的清濑、日本贵族院的渡边畅,长尾景德直接赴台为被检举者辩护;日本法曹界领袖、众议院议员花井卓藏为被检举者单独提出上告书等,这些不仅为被告与台湾民众带来极大鼓舞,也增加了“治警事件”在日本本土的关注度,给予总督府较大舆论压力。
第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庭辩论。民主主义研究学者Anderson指出,殖民地知识分子因受到殖民母国近代化文化的启蒙与洗礼而起来反抗。在“治警事件”的法庭陈述中,这些接受新式教育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善于借助日本国内殖民政策学者的主张,强化议会运动的理论根据,屡屡援引日本国内政界、学界、舆论界的支持言论,抵挡反对阻力,把日本国内所获得的所谓近代化知识理论当作武器,攻击台湾总督的特别统治,不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也必须看到,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对内施行立宪思想,对外施行帝国主义,其国内开明人士对“治警事件”被诉者的支持,是以日本帝国整体利益特别是殖民地利益为考量的。
以“治警事件”表现突出的神田正雄为例。他是大日本主义者,他在“治警事件”中愿意为台湾说话的原因主要是认为 “日本的海外发展主要就是透过殖民扩张。……为使日本民族生存与繁荣的远大理想能够实现,先要努力于殖民地与内地关系的融合。”然而,神田正雄也明白表示,他是把台湾议会当作主义而赞成的人,他并不认为这样的希望马上就要实现,而相信先将地方自治具体化实行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主张渐进主义。也就是说,神田正雄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支持是服从于日本对台湾长久殖民统治的目标。
“治警事件”中为被诉者辩护的日籍律师们的基本立场亦是维护日本的殖民利益。例如,辩护律师清濑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是位极端矛盾性的政治人物。他在日本战前是自由主义派议员,在“治警事件”中基于自由主义,力陈台湾人请愿运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他还是坚持维护日本殖民主义的立场,将朝鲜的民族独立运动视为“阴谋”。日本战败后,清濑在东京大审判中担任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并在担任众议院长时强制表决通过1960年代的日美安保条约。另一个辩护律师渡边也一样,他同情殖民地台湾,却否定朝鲜的独立运动,表示“朝鲜人民只要了解旧日情景者,应该对我们感激涕零才是,然而今日或高呼独立,或要求民族,真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换言之,无论是清濑或渡边,都容忍“合法”的殖民地民族运动,而否定“不合法”的民族自决或独立运动。
因此,台湾民族运动者这种寻求“民主派殖民者”协助,进行体制内抗争的路线,先天上便存在不足,处于被动的危险。因为法律与制度是殖民者所控制的,遵循着殖民者所订定的游戏规则来与之周旋,殖民地人民如翁中之鳖,生杀予夺,操之于人。而这种路线的代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15次的请愿过程中,遭众议院否决7次,贵族院否决8次,逐渐式微,本身也开始分裂。
(三)“治警事件”舆论斗争所凸显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
在台湾民众与日本殖民统治者抗争的同时,祖国大陆在“次殖民”的悲惨与混乱之中,民族主义逐渐成长,中国人自己发动的革命正在进行。两岸的同根性,所处命运的共同性,决定了祖国大陆革命引起的波动,会对台湾抗日运动的展开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蔡惠如等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多次往返于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传递两岸民族运动的信息,推动两岸民众之间互相声援鼓气。“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凸显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
祖国大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浪潮提供台湾反殖民运动的借镜。在思考如何普及文化以扩大运动群众基础的问题上,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借鉴了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和普及白话文的经验,创刊号即用白话文,强调“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并且设立台湾白话文研究会推动白话文。“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这张邀请卡得要用他们看的懂的语言来写才行。”“治警事件”中,《台湾民报》能够成功的与总督府进行舆论抗争,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并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与白话文的广泛运用密不可分,白话文成为台湾民族运动最重要的书写媒介。《台湾民报》广泛采用白话文,不仅可以更好的启蒙民众,与祖国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也能有效的抵制总督府废除汉文的政策,保卫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
“治警事件”被诉者蔡培火表示:“纵观在此二十年的运动过程中(1914-1934),台湾同胞对日本人争取自由民权、范围广阔、明目繁多,就中有两种欲求最为热切,争取最有力,用心最苦。其一是对祖国眷念的心情,其二是对同胞进步的愿望。”台湾史研究学者尹章义亦断言“若不了解日据时期台湾的祖国意识,就无法了解民族运动本质”。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在“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洋溢着民族主义情操。如《台湾议会请愿理由》反复强调台湾汉族是“有历史的民众”,其“特殊民情”不应被抹杀。台湾文化协会时常宣传的要旨为“汉民族是保有五千年光荣文化之先进文明人,不该屈服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
《台湾民报》亦积极唤起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其创刊词上明确表示:台湾民众是“堂堂的黄帝子孙。”《台湾民报》创刊后对中华文化的介绍、祖国新文学运动的介绍与响应,祖国概况的报道与讨论等均不遗余力。《台湾民报》“治警事件”公判号详细记载被诉人士的法庭抗辩,这些言语充满了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正气。如蒋渭水强调“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是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陈逢源表示:“若要排斥中华的文化,人民必起反抗心。所以若视汉民族如视琉球那般没有文化和历史的民族一样就错了。”在“治警事件”的报道、评论中,《台湾民报》屡屡出现“我华民”“我中华民族之台湾人”等字眼,所刊登的被捕人士用中国古诗词改写的入狱诗,传递着他们浓厚的家国情怀。“印刷资本主义对想象共同体具有无比的重要性。”经由《台湾民报》的舆论动员,台湾民族运动人士与一般民众之间,形成一个以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为基础,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想象共同体”。
总督府警务局感慨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牢不可破”,认为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多数人以支那的观念为行动中心”,将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对支那的将来抱持很大的嘱望。……因此民族意识很强烈,常时追慕支那,闭口就强调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励民族的自负心;另外一种是对支那的将来没有多大的期待,重视本岛人的独立生存。……然而,即使这些人也只是对支那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将回复如前者的见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蒋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属于后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禄为主。这段分析表明,无论是“祖国派”还是“自治主义派”都是以中华民族意识为基础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正如“治警事件”亲历者叶荣钟所说:“台湾民族运动的目的在于脱离日本的羁绊,以复归祖国怀抱为共同的愿望,殆无议论余地。”
尽管有些台湾研究者认为,在日据时代已逐渐形成“台湾意识”,甚至有“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然而,日据时期的“台湾意识”是相对于“日本意识”而言,“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另一面意义是在表示“台湾不是日本人的台湾”。因此,当时的台湾意识,不但未排斥“中国意识”,反而以“中国意识”为内涵。“在这种‘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结合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意识’成为界定‘台湾意识’的性质。”台湾的抗日运动不仅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也是台湾同胞认同祖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不仅台湾民众心心念着祖国,祖国亦关注“治警事件”,并进行舆论声援。
治警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的台湾尚志社同仁分别于1924年元旦、1924年1月12日、1924年1月30日召开大会,或发表宣言,或做成决议书,反对总督府的无理暴虐行为。《华北台湾人大会宣言——为“台湾民选议会情愿团”被拘禁而鸣》写道“华北台湾人大会已全体决议,以实力支援贫弱稚嫩的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及期成同盟,务使诸位先锋能够进行猛烈、暴动的大众运动。”上海的台湾青年会将“吾人认为此次台湾当局拘禁台湾议会请愿者六十余名为不当”的决议文附以趣意书,寄发给总理大臣等人。厦门的台湾尚志社同仁做成“反对历代台湾总督之压迫政策!反对台湾总督府对议会请愿者之非法拘留”。的决议书,分发于台湾岛内、祖国各地及东京的关系同志等。
“治警事件”二审判决大部分被告有罪之后,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杂志《共鸣》发表激昂的评论“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多位委员已被宣告徒刑。……台湾同胞,觉醒吧!以诸位的血泪、换取诸位的自由吧。中华同胞,觉醒吧,觉醒吧!勿为日人离间之计所欺矇。”
祖国大陆媒体亦关注“治警事件”,“中国诸大新闻前后数回皆报道,其消息很详细,同情的评论也是多的。”如1925年3月11日,《上海新闻》、《民国日报》分别刊登《台湾自治运动失败 运动者下狱之由来及真像》《日政府对台湾民众运动之高压》的报道,内容均来自“台湾特别通讯”,描述被捕者入狱情形以及该事件来龙去脉,并评价“夫以第三者之观察,该会之行为及经过,由事实法理两论,均不见其有构成犯罪理由。”
对于祖国大陆的支持,《台湾民报》亦积极多次给予报道,让台湾民众知道他们并非孤军作战,“自‘台议’事件发生之后,反动了住华同胞的义愤,前会接及上海、厦门学界的宣言书、最近又接北京华北台人大会的宣言,句句情热,令人悲痛扼腕。”
祖国大陆这些支持“治警事件”被捕者的公开宣言以及报道,频繁出现在台湾和东京都不可能发表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的激烈抨击,以此提高支持被检举者的声势,将祖国大陆反帝民族运动的激情传递给了台湾,凸显两岸血浓于水、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
五、结语
日据时期台湾非武装政治运动在内涵上具有近代政治运动的特质——以争取政治权力为运动的首要目标,在精神上固守民族情操,因此可说是属于近代民族运动的脉流。“治警事件”之所以成为台湾非武装斗争政治运动的顶峰,其贡献不在于政治目标的获取,或是统治者的具体让步,而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向殖民者抗争的精神,锲而不舍地争取台湾人的权利,一再凸显台湾人所处的被压迫处境,进而唤起被殖民者的觉醒与反抗,在这过程中,《台湾民报》成为这一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并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互相声援配合,将台湾统治的根本问题在公共场合提出讨论,与这个运动密切相关的一些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如三权分立、议会政治、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籍此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对当时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民主思想的启蒙,有很大的助益。经过“治警事件”,台湾民族运动人士强化其对中国民族运动与日本社会运动的认知,并且消除民众对殖民地警察的恐怖感和无力感,在凝聚台湾民众民族意识及团结上,产生巨大影响,也为1920年代后半期激昂的农民斗争奠定了基础。
蔡培火强调“台湾民族运动的思想要素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压制、榨取与歧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而增强对祖国的民族向心力所凝结而成的。”[82]“治警事件”是台湾民众在一个近乎市民社会雏形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近代型民族抵抗运动。日本将殖民地台湾视为经济上的榨取区与军事上的南进据点,台湾民众在被奴役和被榨取的过程中,基于对本身的不幸地位及对世界情势的了解,激发了他们对殖民地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他们所使用的舆论斗争的武器,主要来自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祖国反帝民族运动的思想方法以及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启蒙。台湾民众对祖国的眷念之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总督府对台湾民族运动人士进行政治迫害的反衬下,更见强韧,这种浓烈的汉族意识无疑使台湾民众在在对抗异族统治时,拥有强固的团体感。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中反帝、反侵略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台湾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16BH1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
注释
周姚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第9页。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
蒋朝根编著:《狮子狩与狮子吼:治警事件90周年纪念专刊》,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14年,第2页。
周姚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第83页。
谢南光:《谢南光著作选》,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
倪延年:《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台港澳卷)上册》,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若林正丈著:台湾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读会译,《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播种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第70页。
谢春木:《台湾人の要求》,台北:台湾新报社,1931年,第14页。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 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 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中译版》,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周姚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第77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314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120页。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台湾议会之起诉事件(译三月十六日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民报》1924年4月11日。
《时事短评》,《台湾民报》,1924年3月21日。
《台湾总督府的无理解——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台湾民报》1924年12月11日。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4年12月11日。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39-240页。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
《検挙された 臺灣議会請願運動 知識階級七十餘名 治警法違反として》,《朝日新闻》1923年12月25日,大阪、朝刊、3P.
蔡培火:《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71年,第76-77页。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创刊词》,《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
蒋渭水:《五个年中的我》,《台湾民报》1925年8月26日。
《时事短评》,《台湾民报》,1924年3月21日。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5年4月11日。
《治警法第四囘公判(タ刊續き)/言々句々肺腑を突く 至誠至忠の論告 前後實に五時開》,《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8月2日。
《治警法違反事件公判 英米の植民政策を說き 同化政策を高調した 三好檢察官の論告 ガンヂーの惡い所のみを 眞似る被告等の愚を說く 現在の統治に不滿なる者は宜く臺灣を去れと斷ず》,《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8月2日。
《治警違反事件の公判 本島の內治獨立を畫策し 輕舉盲動する一味十八名》,《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7月26日。
《治警违反事件公判——被告等之陈述》,《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7月29日。
《治安警察法违反嫌疑事件之公判——检事求邢》,《台湾民报》1924年8月11日。
《这句话非同小可!》,《台湾民报》1924年11月1日。
《治警法違反控訴公判(タ刊續き)伴野裁判長の 峻烈な訊問に 要點を抉ぐられ 被告孰も苦い辯解》,《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10月16日。
《治警違反事件控訴公判 (タ刊續き)清瀨辯護人 大聲を發して 裁判長から注意を受け 檜舞臺其儘の大見得を切る》,《台湾日日新报》,1924-10-18。
《治警法違反事件の判決終つて 退廷する被告の悲哀と喜歡/無罪となつた王敏川(右より三人目)》,《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11月1日。
《旧式之台湾政策》,《台湾民报》1925年1月1日。
《致台湾议会请愿委员会书》,《台湾民报》1924年10月1日。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5年3月21日。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4年12月11日。
《本报的自祝并对一万读者的祝辞》,《台湾民报》1925年8月26日。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蒋朝根编著:《狮子狩与狮子吼:治警事件90周年纪念专刊》,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14年,第132页。
蔡培火:《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71年,第127页。
《这是谁的善变呢?》,《台湾民报》1924年7月28日。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123-319页。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4年11月21日。该《编辑余话》为中文,“出张”为日语汉字词,即“出差”之意,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经常会将日文中的汉字词直接拿来使用。
蔡培火:《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71年,第2-313页。
《清水街之演讲会》,《台湾民报》1924年11月21日。
《治警牺牲者之出狱》,《台湾民报》1925年6月1日。
《社会改造和我们的使命》,《台湾民报》,1923年7月15日,第四号。
蔡培火:《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台湾文献》1965年,16:02,第175页。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83年,第115-116页。
《林呈禄的供述》,《台湾民报》,1924年9月1日,第二卷第五十号。
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86年,第34-43页。
《台湾议会请愿设置请愿理由书》,《台湾》1922年5月,第9页。
[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 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年,第125-144页。
神田正雄:《動きゆく台湾》,东京:海外社,1930年,第295-302页。
神田正雄:《動きゆく台湾》,东京:海外社,1930年,第295-302页。
《清濑法学博士的辩论》,《台湾民报》1924年11月11日。
渡边畅:《朝鮮司法界に対する回憶》,《朝鲜司法协会杂志》,1924年第三卷,第4-5页。
《创刊词》,《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
[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 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 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 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中译版》,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13-224页。
《创刊词》,《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
黄秀政:《lt;台湾民报gt;与近代台湾民族运动》,台湾:现代潮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蒋渭水氏辩论》,《台湾民报》1924年9月1日。
《陈逢源氏的供述》,《台湾民报》1924年9月1日。
[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 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年,第80-144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7页。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苏硕斌:《活字印刷与台湾意识:日治时期台湾民族主义想象的社会机制》,《新闻学研究》(台湾),2011年第109期,第1-42页。
陈昭英:《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学》(台湾)1995年,第273号,23卷第9期。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127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123-124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诗琅译:《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湾:稻乡出版社,第135页。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4年3月21日。
《日本对台湾民众的高压》,《上海新闻》1925年3月11日。
《编辑余话》,《台湾民报》1924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