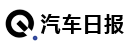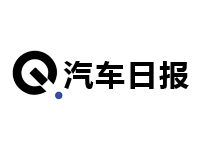自媒体矩阵大PK:垂直内容VS大众内容,哪个更香?
迅猛发展的数字时代背景下,自媒体矩阵已成为互联网内容制作及传播中的重要角色。然而,面对海量信息的冲击,自媒体行业正掀起一场热议,聚焦于特定区域的内容创作至关重要。以下文稿将从多个角度深入解读这一问题。
1.自媒体矩阵的定义
首当其冲是理解自媒体矩阵的内涵。这是指通过各类网络媒体平台进行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的传播,吸引用户,扩大影响力与收入的一种传播途径。这类媒体平台包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知乎及抖音等等。
2.垂直内容与大众内容
自媒体矩阵模式下,内容呈现两类:专业化的垂直领域以及广泛适用于普罗大众的公众导向内容。前者针对某专项领域或特定人群进行深度探索,如科技、健康、美食等,而后者则将传播对象面向更广大受众群体,使得信息更加精炼易懂,例如八卦娱乐、轻松幽默及实用生活知识等。然而,在搭建自媒体矩阵过程中,到底哪种类型的内容应当被选为基地主旨呢?
3.垂直内容的优势
相较于广泛而泛滥的公共内容,专属性强的垂直内容有着显著优势。首先,深度专业探索能够塑造该领域的专业形象并构建口碑;其次,针对性的传播内容可精确触达特定受众群体,培养稳定的忠实用户群;再者,专注于垂直领域的创作使原创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大的展示空间和公众认可。
4.大众内容的吸引力
然而,普及性内容在吸引力上展现出了显著优势。相对于专业化领域的深层探索,普及性内容往往更易于引起共鸣并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其影响力尤为突出。另外,普及性内容往往容易吸引流量和聚拢公众注意力,因而能够迅速积累大批忠实粉丝。因此,在策划和建设海量自媒体矩阵的选题过程中,不应过分强调深度或专业性,而应注重普遍受众群体的需求与兴趣。
5.如何选择合适主题
根据个人兴趣、专业背景以及市场需求,精确选择研究主题至关重要。对于具备专长或深感兴趣的领域,以此为方向固然具备优势;而若擅长以轻松幽默之笔触传递生活心得,或具备引导热门话题讨论之才能的个体,主导公众关注的主流议题也颇具探讨价值。
6.垂直与大众并重
并非仅需择其一,实践证明,成功运营自媒体矩阵的众多实例,皆均衡展开纵深及广度双面内容。通过多元平台发表各类情态的文字或视频以迎合多样化受众需求,进而扩大用户基础。故此,不应局限于单一主题类型,而应兼收并蓄各元素以灵活创作。
7.内容质量至关重要
无论呈现何种题材,确保内容品质始终是自媒体创作之核心要素。拥有专业知识或是创造趣味性内容,需通过精妙设计和细致制作方可获得读者喜爱。高质量的稳定输出有助于巩固粉丝基础并增强影响力。
8.总结
总之,自媒体矩阵的选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市场需求周全考虑,但无论何种取向,原创性和质量始终是必要因素。最终的追求在于打造个人鲜明的品牌形象,并且与广泛读者建立稳固的互动联系。
罗昕:职业化与规范化:创作者经济中的“自媒体”治理
作者:蔡雨婷(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罗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9期
导 读:
“自媒体”治理涉及政府、平台、行业、社会四大关键利益相关方,应形成多重监管体系和综合治理路径,推动“自媒体”职业化、规范化并嵌入基于平台的创作者经济浪潮中。
自“人人皆可传播”的Web2.0时代以来,“自媒体”的勃兴促进了社会的文化生产,却也带来了内容生产把关的失控,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失序。从微博、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到抖音、快手,“自媒体”发展始终存在“内容乱象”顽疾。各领域“网红”不断涌现,使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更加复杂。从全球内容生产变革的视角看来,“自媒体”行业属于正在涌现的“创作者经济”的典型代表。“创作者经济”指创作者通过创作内容,获得粉丝,并以此赢利的经济行为[1]。应将“自媒体”视为一种形成中的新职业,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专业规范、职业道德,实现他律与自律。同时,数字传播平台的崛起重构了传播权力,“自媒体”的内容生产深受平台逻辑影响,“自媒体”治理离不开对平台权力的审视。
创业解决主义:“自媒体”职业化的驱动逻辑2020年,国家多部门联合发布16个新职业,“全媒体运营师”位列其中。媒体运营师包括创意策划、视听运营、直播运营、流量优化和数据分析5个职业方向,“自媒体”从业者的工作内容广泛涉及这些职业方向。从职业能力看,“自媒体”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成为“全媒体运营师”。根据功能不同,可将“自媒体”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内容创作类“自媒体”(如微信公众号),二是表演类“自媒体”(如网红)。迈克尔·基恩和陈颖用“创业解决主义”一词来描述一种将数字技术视为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促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方式的倾向[2]。国家创业政策的引领、市场机会及个人的新职业探索,促进了“自媒体”行业的发展。
(一)创作目的转型:从“表达自我”到“职业谋生”。“自媒体”一开始是以信息技术对普通人的“传播赋权”姿态而出现的,“We Media”一词生成于“参与式民主”的话语形构中[3]。博客、社交媒体为公众的自我表达和参与公共讨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短视频媒介更是使个体表达和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带来了“无名者的出场”和全民记录的勃兴,普通人也拥有被看见的可能[4]。在微信公众号兴起期,就出现了一批职业“自媒体”人。短视频兴起后,注意力经济更加盛行,各平台网红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社会大众将“自媒体”视为一种赚钱谋生的新途径,“自媒体”行业不断发展,同时出现矩阵号、MCN机构等专业运作机制。
(二)创作主体扩大:下沉市场催生“不可能创意阶层”形成。近年来,随着用户规模增速的放缓和市场的下沉,“自媒体”网红呈现出两个鲜明的发展特征。一是地域化。网络涌现出一批地域网红或话语模因,如“甘肃不大,创造神话”。二是全年龄化。如一批以“奶奶”“姥姥”为主角的乡村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关注者众多。Jian Lin和高伟云提出了“不可能创意阶层”的概念,意指短视频平台的可供性让居住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多元化、往往被边缘化的中国人成为原本大概率难以成为的创意工作者[5]。当下,“自媒体”群体呈现出数量多、空间广、群体异质性高等特征。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内容创作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三)创新过程专业化:自我学习与业内培训。与“自媒体”野蛮生长的业态和日渐庞大的从业人员相对的是,专注于新媒体从业人员培养和创业的学校教育和来自官方的培训渠道供给不足。国内新闻传播教育跟传媒产业数据化、融合化、平台化、智能化的现实趋势仍有差距,教育与产业脱节明显[6]。在此背景下,部分“自媒体”新人通过自我学习或学徒制的“传帮带”来积累从业知识,业内培训和民间课程广为流行。这些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使创作者熟知平台规则以更好获得流量。许多从业者会自主传播有关算法的民间理论,即“算法八卦”[7]。产业链不断完善,“自媒体”团队的内容制作能力不断提升,吸引受众的手段也愈加丰富。然而,上述培训多重视表层的业务教学,缺乏深层的理论素养、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学习,同时也缺少职业道德教育,使从业者的能力和素养发展不全面。
(四)创作手段升级:平台可供性降低创作门槛。对于创作者而言,平台的可编辑、可连接、可货币化是三个最重要的属性,分别指向了内容产业的生产、分发、变现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可编辑。“自媒体”平台在准入规则、功能、页面、符号表达等方面设置了简便易行的规则,用户发布内容不仅难度降低,内容的表现力也得到增强。短视频平台凭借傻瓜式操作为创作者赋能,提供了剪辑、配乐、特效、字幕、滤镜等实用功能。最近,AIGC被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覆盖图文、短视频等多个领域。二是可连接。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平台集中了大规模的生产者、消费者,掌握了流量。算法使信息更精准地触达目标人群。通过流量补贴,平台提升了特定内容的可见性,打造“爆款”成为可能。三是可货币化。“自媒体”有多种收益方式:平台分成、平台广告嵌入内容、创作者自营广告、受众打赏等。不少平台为了激励创作者,推出优质作者资金扶持计划。平台可供性降低了创作成本,优化了用户的观看体验,但也诱发了网络沉溺现象。
流量畸变:创作者经济中的内容风险表征流量逻辑是网络传播平台生态系统运作的核心逻辑。它指的是平台和“自媒体”需要持续地吸引用户或粉丝的关注和参与互动,流量越多,潜在商业价值越大。流量逻辑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自媒体”过度追逐流量,而平台往往是“导致流量至上的最大推手”[8],造成了网络空间中的内容风险。
(一)深度伪造虚假信息,“新黄色新闻”污染信息环境。随着研究深入,学界倾向用“虚假信息”“欺骗性信息”“谬讯”(disinformation)指有意造假和传播的假信息,用“误导信息”“误讯”(misinformation)指并非故意生产或传播的错误信息。部分“自媒体”使用多种手段传播虚假信息。
一是编造。“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通过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等手法,制造虚假或真假参半的内容。二是仿冒。一批未具新闻传播资质的“自媒体”账号仿冒政务机关、权威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主持人或记者,并擅自使用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理名称,误导公众。三是摆拍。摆拍短视频一般诉诸情绪,针对社会热点虚构故事情节,挑动大众的愤怒、同情、焦虑、爱国主义等情绪,“收割”流量。一些网红团队在贫困地区开展“卖惨带货”“悲情营销”,甚至误导一些专业媒体加以转载。四是深度伪造。AI、合成媒体等技术被应用于内容造假之中。AI换脸和拟声技术不断迭代,全球虚假信息生产进入深度造假的阶段,眼见不再为真。利用开源、免费的软件,普通人可以轻松制作换脸视频。2022年,抖音以“滥用平台道具”“仿冒虚假人设”为由封禁了一个名为“俄罗斯娜娜”的账号,该账号疑似使用AI特效,仿冒外国人来博取关注。
(二)炒作时事热点,误导公众认知。一些“自媒体”利用当下的社会心态,选取一些博眼球的话题大肆炒作。尤其是一些网络大V利用自身影响力,向粉丝传递错误观念、错误价值观。“自媒体”炒作的话题主要在于两方面。
一是炒作热点话题。健康、教育、食品安全、性别等议题是广受关注的公共话题。过去几年,网络上陆续出现炒作女性身材标准的话题,如“A4腰”。同时在“反身材焦虑”的网络争论中,一些信息发布者挑起男女对立,使信息更加芜杂、极端。二是炒作时事政治。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一些大V在利益驱动下成为其鼓吹手。围绕“爱国”“恨国”两个二元对立的话题,“自媒体”可以轻易掀起不同群体的争论。
相比于可以辟谣的虚假信息,炒作内容往往真假参半,事实和观点混杂,在误导公众认知和价值观上的隐蔽性更强。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战争发展出“认知战”的新形态。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与国外力量联动,发起认知战,炒作时政和社会话题,激起人们对政府、社会的不信任。
(三)过度宣扬消费主义理念,传播不良价值观。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把消费视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唯一实现路径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9]。部分“自媒体”网红大力宣言名车、豪宅等物质生活,打造“呼风唤雨”的“社会大哥”人设,影响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中国社科院相关报告指出,未成年人刷短视频越频繁,价值观取向越受影响:他们更注重财富、名气和外表等外在价值取向,降低对个人成长等内在价值的关注度[10]。
当下网络空间中,“色、丑、怪、假、俗、赌”等违法违规内容不时出现。例如,自诩“女讲师”的某博主宣扬“三句话让异性为我花钱”,与独立、自尊的价值观相悖。一些“自媒体”热衷于发布扭曲“三观”的“土味”说理,面向老年用户散播“养儿养女无用”等歪理邪说。此类言论放大了社会阴暗面,长此以往,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尊崇将弱化。
(四)社会责任感缺失,不当进行流量变现。为了流量变现,部分“自媒体”罔顾社会责任,诱导、欺骗粉丝。一些主播彼此之间热衷于直播打PK,联合演戏诱导粉丝“刷票”。部分“自媒体”不顾公德,扰乱社会治安。2023年8月,河北多地遭遇洪涝灾害,某些网红却在救援现场摆拍作秀,“消费”灾难。部分网红不能严于律己,为了持续获得关注而剑走偏锋。某云南网红凭借方言说唱走红,曾参与官方举办的旅游推介活动,一年后却发布涉黄信息,被平台封禁。
随着网络用户下沉和用户画像细分,“自媒体”面向特定群体精准“收割”流量变得更加容易。2023年8月,抖音博主“一笑倾城”“秀才”相继走红,二者仅通过对口型唱歌,就赢得了大批中老年网友的喜爱,双方的直播PK被称为“掏空一个省的养老金”。然而不久后,“秀才”因违反平台规则被封禁。据媒体报道,多名中老年女性网友称被其诱骗打赏,包括打赏价值近52万元的礼物。某些不良网络文化已经影响现实生活中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迈向职业规范的“自媒体”综合治理路径在对数字平台的研究中,流量逻辑往往被等同于不道德的流量追逐行为[11]。对“自媒体”传播失范的关注不应只停留在道德层面,而同时应看到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推动,以及平台在顺应国家意志和追求利益之间对“自媒体”的弹性引导。平台中的“自媒体”治理涉及政府、平台、行业、社会四大关键利益相关方。未来,“自媒体”发展与治理将嵌入创作者经济浪潮中,而“自媒体”作为一种职业也将与平台共生,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规范。
(一)政府监管:加大监管力度,创造“自媒体”职业发展良好环境。内容生产平台化趋势下,“自媒体”监管形成政府、行业协会、平台、MCN机构或“自媒体”组织、“自媒体”个人的层层责任传导机制。(见图1)近年来,国家各部门密集出台涉及“自媒体”治理的政策法规,覆盖微博客、音视频、直播、账号、MCN机构、主播、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网络侵权等多主体多层次,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2023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从资质认证、信息来源、账号运营等多方面作出全链条管理规定。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自媒体”传播规范治理的系统性规范文件。
图1:“自媒体”监管责任传导机制
下一阶段,需要各地部门履行属地管理责任,依法实施监管。在“政府—平台—用户”的动态监管过程中,平台是否严格监管主要取决于政府惩罚强度[12]。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对网络传播平台的惩罚力度,鼓励第三方媒体监督平台,增加平台消极监管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以此促进平台规范自身行为。政府还应通过反垄断管理,限制平台权力,督促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除了规范监管,各地政府还可以牵头组织高校、行业等多方力量推进“自媒体”人才教育和培训,促进“自媒体”的职业化、规范化,营造“自媒体”职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
(二)平台履责:构建覆盖全域全链条的治理装置。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内容治理方面承担主体责任。“自媒体”寄生于平台,在流量逻辑下,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谋,给予部分灰色内容生存空间。平台的治理装置是指“一种专注于流通的治理形式,其目标是以维持平台的方式监管内容的流动”[13]。托马斯等总结了平台治理的三项策略,分别是政策制定、内容策展和内容审核[14]。
首先,平台通过标准、指南和政策的制定来对“自媒体”内容和行为作出总体规范。从API接口、软件工具开发包到内容长度、图片格式,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影响着内容生产和分发。平台的社区指南等政策则对用户的内容生产和互动行为作出规定。内容平台应改善架构和社区政策,多方面规范“自媒体”行为,促进平台参与者与平台目标对齐。广告分成机制是最核心的平台政策之一,平台应将广告收益向优质内容创作者倾斜。
其次,平台可以通过内容策展,对内容和服务进行排序来控制特定内容的可及性和可见性。内容策展涉及算法推荐与人工编辑的平衡问题。实践证明,将内容把关完全交由算法将带来“信息茧房”“网络极化”“算法歧视”等一系列问题,人机协同才是有效管理方式。《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促进算法应用向上向善。平台应持续优化算法,防止内容风险。随着技术发展,AIGC将带来内容生产的大爆发,平台要运用算法限制AI生成和传播低质、有害的内容。
最后,内容审核是指对平台对内容和账户进行预筛选、拒绝、移除、封存、禁止、降级或去收益化。例如,YouTube平台使用“黄标政策”来对内容作出限制:视频被标注绿、红、黄三种颜色,以此决定是否可以获得广告分成。算法审核和人工审核同样是两种重要的内容审核方式。平台应通过外包等方法增强内容审核力量。研究显示,中国的在线内容提供商更多使用屏蔽、删除等方法管理内容,而这种措施往往与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形成张力[15]。国内平台可更多使用社区规范等方式提前对内容创作者进行教育和引导,同时提升平台政策的可理解性。
(三)行业自律:树立专业理念,增强职业规范。“自媒体”具有门槛低的特点。正规职业教育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规范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缺乏。有学者提出,可以从组织专业主义与职业专业主义两个维度引导“自媒体”专业理念建构[16]。
组织专业主义代表一种规范性控制。行业的规范性控制主要来自行业协会和MCN机构。行业协会应积极制定具体的行业规范作为法律法规的补充。如中国广告协会制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制定《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中国演出协会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国内MCN机构数量超24000家[17]。MCN机构应加强对旗下“自媒体”的创作指引。例如Papitube公司内部的作者管理部实行制作人制度,对博主的选题规划、人设等全面负责。“自媒体”机构应借鉴传统媒体机构,进行“反向融合”,建立编导责任制、内容审核制等规范制度。
职业专业主义指向了一种意识形态控制。“自媒体”行业群体要建立自身的专业理念和职业规范。一方面,是建构专业话语,建立合法性。“自媒体”在内容生态中有其独特定位,采取窄众化传播、聚焦知识专业性或亚文化调性,促进智识生产、社群建构等是其主要特色[18]。另一方面,是内容生产专业规范。加强监管后,“自媒体”创作也渐趋规范,如许多“自媒体”在创作虚拟情节作品时会标注“剧情演绎”等字样。创作者大会等社群交流能帮助“自媒体”行业从文化层面建立职业自律的默会知识。各平台、各领域的头部“自媒体”应以身作则,培养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
(四)社会参与:完善网络参与机制,提升监督效能。在网络内容生态系统中,有着许多利益相关方。除了政府、平台、“自媒体”,还包括广告主、主流媒体和普通用户等。
广告主通过广告投放决策,影响平台与“自媒体”的盈利。当特定平台上的有害内容传播问题久未得到改善时,广告商应拒绝在其上投放广告。主流媒体可通过新闻监督、效果评价参与“自媒体”内容协同治理。除了曝光与监督,媒体还可发挥智库角色,参与“自媒体”治理的决策制定和效能评价。2019年起,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成立课题,通过数据测评、深度调查、行业分析等方式,持续观测网络内容生态治理,先后推出百余篇报道和多份研究报告,广受社会关注,推动政府部门实行监管。普通网民有多种途径参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一是提升媒介素养,提高辨别能力,不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二是积极通过各类渠道举报违法不良信息;三是深度参与违法不良信息治理,如参与相关民间组织。抖音平台建立了大众评审员机制,普通用户满足条件并通过考试后,可申请成为大众评审员。平台提供多渠道的讨论、参与和协商机制,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有助于遏制“自媒体”乱象,共同构建良好的网络内容生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竞争格局与中国进路研究”(批准号:18AXW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莫梅锋.互联网“创作者经济”的规范化发展[J].人民论坛,2023(06).
[2]Keane M, Chen Y. Entrepreneurial solutionism,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hinese drea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19(06).
[3]於红梅.从“We Media”到“自媒体”——对一个概念的知识考古[J].新闻记者,2017(12).
[4]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J].国际新闻界,2020(06).
[5]Lin J, de Kloet J.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J].Social Media+ Society,2019(4).
[6] 黄升民,刘晓,刘珊.中国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困惑与走向[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05).
[7] Bishop S. Managing visibility on YouTube through algorithmic gossip[J].New media & society, 2019,(11-12).
[8]胡泳.全球开放互联网的歧途[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23:72.
[9]韩喜平.消费主义思潮泛起的成因及引导[J].人民论坛,2021(04).
[10]陈磊.调查显示未成年人刷短视频越频繁价值观取向越受影响[EB/OL].中国新闻网.(2022-12-26).
[11]Chen C, Wang Z, Gn J. Serve the Traffic: The Logic of Traffic and Its Politics on WeChat Platform[J].Social Media+ Society, 2023(3).
[12]巩永华,何光强.静态和分级惩罚机制下短视频平台监管策略的演化博弈研究[J/OL].科学与管理[2023-09-20].
[13]Siapera E. Platform Governance and the “Infodemic”[J].Javnost-The Public,2022(2).
[14]Poell T, Nieborg D B, Duffy B E.Platform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M].John Wiley & Sons,2021:84.
[15]Einwiller S A, Kim S. How online content providers moderate user‐generated content to prevent harmful online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of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J].Policy & Internet, 2020(02).
[16]蔡润芳,汤乐盈.“竞争性选择”:两种形式下商业自媒体的专业理念“重构”——基于对“当下频道”的田野调查研究[J].新闻记者,2021(11).
[17]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2021-2022)[R/OL].(2022-07).
[18]张志安,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J].新闻与写作,2018(03).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蔡雨婷,罗昕.职业化与规范化:创作者经济中的“自媒体”治理[J].青年记者,2023(19):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