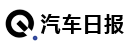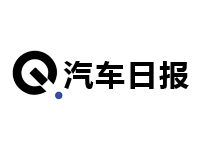鲁迅最喜欢的《孔乙己》:看别人笑话时,自身已成笑话
鲁迅先生总是很会讲故事,讲的都是悲剧,而且不止故事里的主角是悲剧,连同所有配角以及围观的人都成了悲剧。
而听故事的人,往往不小心就听到了“某一面”的自己,往往不小心听着听着,自己就是悲剧,听懂了是悲哀,听不懂也是悲哀。
比如他讲“血馒头”的故事,革命者夏瑜被杀,华老栓听说血馒头可以治病,就托人找关系,买到了几个血馒头,拿回家去给儿子华小栓吃了,一家人满怀期待,谢天谢地地等着华小栓奇迹般的好过来。
你要是听懂了,就会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是懂了他们不幸在哪,不争又在哪,那么自己身上难免也会有一些那种不幸和不争。
你要是听不懂血馒头的故事,那么自己可能难免也会加入这吃血馒头的队伍中去,不期然地吃了谁的血馒头,那就真的在“被哀”与“被怒”的人群里了。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很多,他讲了一个人,可是那个人的身边,却围绕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
比如写“东京杀头”的故事,一群中国人在围观呐喊,比如他讲“祥林嫂”,身边就有无数人看祥林嫂的热闹,他写阿Q,阿Q就是热闹,可是看热闹的人,又是别人的热闹。
他讲孔乙己的故事,很多人就只看到了孔乙己的“笑话”,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笑话。
还记得孔乙己吗?
在鲁镇的酒店里,穿长衣的“长衣帮”阔人去喝酒,坐着,而且会点几个小菜,而穿短衣的“短衣帮”穷人去喝酒,往往是要站着喝酒。
孔乙己是唯一的穿着长衣却站着喝酒的人,以前看,觉得这是“死要面子”,但后来发现,穿衣无错。
孔乙己是读书人,可是好吃懒做,也考不上功名秀才,所幸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便帮人抄写书本度日,可是他又懒,不愿意劳动,抄着抄着,往往书本笔墨一起“不见了”。
久而久之,便没有人找他抄书,他不得不做些偷窃之事,可是当别人说他偷书时,他说“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又说什么君子固穷,这是明显的强词夺理,干了错事还死不承认。
后来被打断了腿,还不知“悔改”。
美学家刘再复如此形容孔乙己: 贫贱而悲惨的“多余人”,失去人的尊严与资格,被社会所耻的下层知识分子。
真正的“人间失格”。
可是“孔乙己”之所以是一个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的“偷窃”“无能”“好吃懒做”,我们还要把目光往他周围一看,看看那些看热闹的人。
那些没有同情心只觉得“热闹不够大”的看客,那个始终只惦记着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的酒店老板,那个“长得很傻”的小伙计,他们对于孔乙己的遭遇,只是当做热闹来看,麻木,没有人情味,冷漠,无情。
他们看孔乙己的笑话,却不懂孔乙己的悲剧,更加不懂自己的悲剧。
人喜欢热闹没错,但是喜欢看别人的热闹,这就是一个毛病。
能让自己的人生热闹起来,这是一种能力,可是自己的人生热闹不起来,就专找别人的热闹看,这就是大大的问题。
前两年“流浪大师”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流浪大师”拾荒为生,喜欢读书,长发凌乱,衣衫破烂,身上脏兮兮的,却往往口吐妙语,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历史。
很多人得知这样一位“妙人”后,纷纷围观,有人采访他,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拍视频,“流浪大师”被围观成一只“猴子”。
最后烦不胜烦,读书再多,也经不起这样的围观,他不得不一再声明,他不想被采访,不想被围观。
看了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不新鲜了,没有热闹可看了,又伸长脖子等着,有人说他是“当代孔乙己”,实在是因为他是穿长衫却“落魄不堪”的人。
要我说,“孔乙己”不再是孔乙己,但围观看热闹的人,还是围观看热闹的人。
孔乙己好吃懒做,“流浪大师”只是把流浪作为生活方式而已。
“流浪大师”是知识分子,可是他和孔乙己不一样,他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没有拿不正当的钱,也没有摆出读书人的架子。
可是围观的人呢?
据我所知,他们并不是理解了“流浪大师”为什么会成为流浪汉,也不是理解了为什么一个流浪汉坚持读书,他们就是见到了一个流浪汉,却在读书,而且读书可能比很多人还要多,所以他们觉得新鲜,觉得有趣,就好像在一群鸡里看见了一只鹤。
他们自己的生活无聊了,自己又没办法有趣,所以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别人的乐子”。
就像那个《孔乙己》里面那个小伙计说的:“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
只有孔乙己来了,才能笑几声。
鲁迅先生若是见到现在这种场景,大概还是会说,是不是孔乙己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热闹的人还在。
喜欢看热闹的人有一个特点,见不得别人好,因为别人好了,就没有乐子了,有的是普天同庆,只有别人“不好”的时候,乐子才会出现。
取笑别人,看别人窘迫不堪,看别人无地自容,看别人死于非命,才有谈资,才觉得见过了不一样的世面。
只有在看热闹的时候让别人无法可说,觉得自己是见证奇迹,那才是真正的热闹。
孔乙己站在台前教那个小伙计写茴香豆的“茴”字,那个小伙计想的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哎呀,孔乙己是一个讨饭一样的人,所以他的善良,都那么廉价。
这才是热闹。
似乎一个讨饭一样的人,就不配教别人什么。
孔乙己读书,却没能考取功名,就有人取笑他:孔乙己,你真的读过书吗?怎么连一个秀才都考不上?
读书是好,可是在看热闹的人眼里,读书人考不取功名,过得落魄不堪,多好的笑话啊。
而且这一幕,多么熟悉啊!
孔乙己进店,因为偷东西被打伤了,大家就笑得更开心了,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孔乙己不理他们,热闹就没法继续,所以他们说:“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乙己瞪大眼睛,在那里无力地“强词夺理”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看热闹的人继续说:“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直到孔乙己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他们这才心满意足,以胜利者的姿态享受着胜利的果实。
孔乙己买了茴香豆,有孩子的时候,他便一人一粒分给那些孩子。
这是孔乙己善良,可是这可没有什么热闹可看啊。
接下来,那些孩子重新看着孔乙己的盘子,孔乙己便用双手护着盘子嘴里念叨着:“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围观的人又是一阵大笑。
热闹之所以是热闹,是因为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而人要看的就是当事人从理想的高处摔进现实的深渊。
在鲁迅先生的那个年代,现实太残酷了,所以理想特别容易掉进现实。
革命者怀着救国的理想,干着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的事情,被主流势力所不容;很多人怀着高洁的理想,最后也在现实里蝇营狗苟,甚至成为普罗大众里的笑话。
孔乙己可悲吗?可悲!
孔乙己可怜吗?未必可怜。
但孔乙己身边那群看热闹的人,那群一心只想看热闹的人,他们怎么样呢?
我觉得,可恨。
作为芸芸众生里最普通的一个,我十分讨厌别人把我当成热闹来看。
我吃自己的饭,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虽然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每天都很开心。
但是一回家去,一些人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就一副“看热闹”的样子,所以我讨厌。
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看见别人吵架了,一大群人围观上去,劝架的没有几个,火上浇油的倒是不少。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津津乐道。
我喜欢热闹,但是我喜欢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温度,我讨厌看别人的热闹,更加讨厌被当成热闹。
一个人如果需要从外面寻找热闹,就说明他内心空虚。
而一个人如果对别人的遭遇不能理解,仅仅是看热闹,那么他的麻木也可想而知。
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很好地探讨了“看热闹的人”的罪恶。
电视剧中,“精神病人”李晓明杀了不少人,可是律师王敕却在为他辩护,还有为同是“精神病人”的杀人犯陈昌辩护。
可是在不明所以的人眼里,王敕的做法无异于为虎作伥,受害者家属用大便泼在王敕的身上,王敕脸上只有惊愕。
其实王敕是想弄清楚这些杀人犯为什么要杀人,弄清楚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可是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他。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都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的人。
儿子李晓明杀了人,李晓明的父母被无数记者围追堵截,李晓明的妹妹被弄得不敢上学,记者想知道李晓明的父母为什么会教育出一个杀人犯儿子。
李晓明父母自己也痛苦不堪,他们跪在地上请求原谅。
被害人的家属很悲剧,可是杀人偿命,杀人者的家人也很悲剧。
但是更悲剧的是,无数人还在看他们的热闹。
据我观察,大多数能被称为热闹的存在,其实都有悲剧的因素。鲁迅先生文章的孔乙己是悲剧,阿Q也是悲剧,祥林嫂也是悲剧,甚至闰土也是。
看热闹的人,是想站在道德伦理或者常识的制高点审判别人。
可是人最应该审判的,恰是自己啊!
卡夫卡说:“你们凭什么来审判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不能审判别人,可我能够判断自己。”
《我们与恶的距离》还在探讨网络围观的善恶。
有句话说:“你们每天都在杀人,只不过杀人犯用刀子杀人,用枪杀人,而你们杀人的工具,是你们手中的笔,是你们说出来的话,是你们敲出来的字。”
这就是围观者的恶,这就是看热闹的人看出来的“悲剧”。
之前看到不少案例,一些人因为受不了网络骚扰而失去生命。
苏格拉底说,无知是一种罪恶。
这话用来形容“看热闹不怕事大”,很合理。
孔乙己死了,他是不能不死的。
而杀死他的,除了他自己,除了那个时代陈旧的观念,更有他身边那些麻木的人,他们一人一句,戳在孔乙己的伤口上,他们没有想过帮他,所以孔乙己在的时候,就热闹一下,孔乙己不在的时候,日子照样也过去了。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问过鲁迅:“《呐喊》中哪一篇最好?”
鲁迅回:“《孔乙己》,所以译了外国文。”
再问:“好在何处?”
鲁迅说:“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
讽刺虽不明显,但明眼人却一读就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讽刺意味,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才能对别人的苦难熟视无睹,还能任意取笑?
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才能一心只热衷于看“热闹”,而没有人情味呢?
而讽刺最浓重的一笔,恰恰从看热闹的人的笑声中传递出来。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总有那群看热闹的人的身影,他写“祥林嫂”的悲剧,这悲剧却成了别人的“笑谈”,他写阿Q的悲剧,这悲剧竟也成为看热闹的人的“笑谈”,他写杀头,还有一群人围着看。
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今天,这样的看热闹的人依旧无处不在,于是,在这群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成了阿Q,有人成了孔乙己,有人成了闰土。
他们成了别人的热闹,别人又成了别人的热闹。
看热闹的还在,有些事情就永远是悲剧。
在《观斗》里,鲁迅说: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喜欢看热闹的人就是这样,喜欢看别人斗,至于什么缘故,那不重要,斗得越精彩,他们越高兴。
鲁迅先生虽然从医治人肉体的医学转而学医治人灵魂的文学艺术,可是他还是医不好人灵魂的空虚,医不好他笔下的那些“看热闹的人”。
灵魂除了自救,无人可救。
你叫破了喉咙,也只能叫醒那些愿意醒来的人,否则鲁迅就不会说:“假如此后竟没有火炬,我便是那黑暗中唯一的光”;马相伯也不会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能叫醒中国。”
那些热衷于看“热闹”的人啊,醒来吧!
看别人热闹笑话的时候,你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
来源:微信公众平台:“有书”
作者:不有趣灵魂
【声明:本号为“全民阅读推广”官方公益账号,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涉嫌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一个病句,是鲁迅的笔误还是有意为之?
鲁迅先生在《孔乙己》的结尾写了一句颇有争议的句子:“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因为他将“大约”和“的确”连用,意思显得既矛盾又累赘。一直以来,大家为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一次笔误,再伟大的作家也会犯一些小错误,不必大惊小怪;而另一些人则坚信鲁迅先生不会错,当中肯定有更深的理由。
关于鲁迅先生为何会连用“大约和的确”这两个词,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没有什么深度,就是笔误;二、鲁迅用绍兴方言写作,这是附带的特色;三、这是先生自创的“矛盾修辞”。
目前第一种说法已经被否定,因为鲁迅先生除了在《孔乙己》中曾经用过“大约的确”,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Q正传》中也用过“似乎确凿”,并且这些作品都是他的早期作品。
其中《孔乙己》创作于1918年,不但是他早期的作品,也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之一。这篇文章虽然短小,但创作耗费的时间长达数年。
鲁迅先生在生前曾建议别人“不能生造只有自己懂的词汇”。所以,他不太可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犯低级错误。因此,《孔乙己》的最后一句话,“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就是鲁迅先生有意为之了。
一、“大约的确”与方言写作我们平时在阅读与写作的时候,一般嘴里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有留意,会发现我们还是在使用一种语言,在心里“默读”。无论是“普通话”还是自己家乡“方言”,只要不经意地采用了其中的一种,就会对你阅读或者是写作的“语感”产生影响。
比如老舍先生用京味方言创作的小说,一个习惯用南方方言“默读”的人,可能就不如用北方方言“默读”的人读着有味道。而在写作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显得更加突出。
不经意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创作,在文章中加入方言词汇。一些地域特色十分明显的方言语汇,是可以避免的,而另一些不太明显的用语习惯则被保留下来。
鲁迅先生是绍兴人。有人在研究了绍兴方言之后表示:绍兴方言里面有一个四字词组,本来是两个词,合起来的意思就等于“似乎确凿”或“大约的确”。《孔乙己》的作者是绍兴人,而小说的主角孔乙己也是绍兴人。所以,鲁迅故意在文章中保留了“大约的确”。
那么,为什么鲁迅先生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使用方言呢?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他是为了给文章增添一点“生活气息”,让人感觉真实。
好比你写一个四川男人,你不让他骂一句“龟儿子”,四川人读了会觉得你写得不像。因此《笑傲江湖》中,青城派的余沧海和弟子们出场时必骂“龟儿子”。
尽管鲁迅先生一直反对在文章中使用“只有自己明白”的词汇,并且“大约的确”看起来特别像语法错误,可是它的出现,并不妨碍读者对文章本意的理解,所以鲁迅先生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二、“矛盾修辞”和其它“大约”的意思是有可能,而“的确”的意思却是百分之百。鲁迅先生把两词连用,有人说:这一种“矛盾修辞”的手法,是先生刻意为之。
还有人举例子说,这种修辞手法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民间口语中并不鲜见。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宝钗也曾经笑过某人是“无事忙”。再比如我们平时口语中说的“小大人”、“老小孩”。
矛盾修辞常被用于格言警句和一些习惯用语之中,像《孔乙己》这样的用法,既非格言,又不是大众习惯,它和“矛盾修辞”显然是不沾边的。不过,鲁迅先生的确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才采用了这样的句式。
在《孔乙己》的末句中,“大约”是修辞“孔乙己的确死了”。事实上它代表人们对于孔乙己是生或者死的三个不同阶段的看法。
第一个阶段,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用手“走”来喝酒。之后离开酒店,到了年关也都没有再回来。于是大家认为他“可能是死了”。
第二个阶段,又过去了五、六个月,端午节还没有看到孔乙己,老板说他还“欠店里十九个钱”。这时候,大家觉得他“确实是死了”。
第三个阶段,从端午到中秋,从中秋再到下一个年关,还是不见孔乙己。旁人早已经不关心孔乙己的死活了。只有文章中的“我”还一直惦记着他的生死。
可是,一个人穷困潦倒到了他这样的地步,腿也被人打断了,过了一年也没见到人影。“我”不由得开始怀疑:别人的猜测可能是对的,“‘大约’孔乙己的确是死了吧”。
所以,这其实是鲁迅先生故意留下的一个悬念。这个结局就和后来金庸在《雪山飞狐》中留下的开放式结局一样。胡斐死没有?有可能死了,有可能没有死。
孔乙己也是一样。毕竟他前一次被丁举人吊着打的时候,大家就说他死了。不过,他后来仍然能用手“走”来赊酒吃。
结语《孔乙己》创作的时间比较早,而当时正处于新旧文体转换时期,所以有人觉得这是鲁迅先生写错了。可是他是大文豪,他犯下的错误,后人一直在替他掩饰着。但是,我还是认同:鲁迅先生在这里明显不是“笔误”,他就是故意这样写的。
比如,他自己说了不能造生僻词汇,可是他就在《闰土》里生造出了一个“猹”。而语文老师告诉我们,创作中要“避复”。就是要避免同意的意思,不能车轱辘来回地说。可是鲁迅先生偏要写:“家门前有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小时候我特别不服气:凭什么呀!他写错了字就成为了“通假字”,而我写错了就要被扣分,还要挨骂。长大了我就懂了,这件事儿不服气不行,有本事你也去当文豪。
“大约孔乙己的确是死了”这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是鲁迅写的。对于名人的经典作品,普通人都会给予极大的宽容,也会用心去体会作者创作的本意。但是对于普通人的作品,大家更习惯去“喷口水”外加“挑刺”,所以普通作者最好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