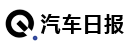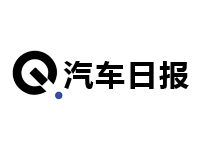汉字的两次大变革:自下而上的“变隶”与自上而下的“简化”
汉字发展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形体改变与其他阶段不同,这两次改变就是:变隶和简化。变隶和简化都是为了让汉字更便于应用。但是,二者所采取的革新方式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自下而上,后者则是自上而下。变隶就是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非形式上的突变或者是人工干预的强制性改变。
通过下图若干汉字的变隶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变化的连续性。
隶变示例(参1)
变隶发生的原因是形体存在与大众使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凸显使得汉字形体不得不朝着大众期望的方向演进。当时的大篆给书写带来了极大不便,大篆形体结构复杂,有些笔顺也是有悖于书写习惯,线条上也缺乏一定的节奏,缺乏明显的间隔停顿。大篆这些缺点给书写者造成极大的不便,难以高效快捷地书写使用。
吴大澂《大篆楹联》选图
大篆又称"籀文",通行于西周晚期的文字,后来为秦所承袭。与其他六国文字相比,秦所用大篆确实更加复杂,象形的成分依然较多。这种复杂的文字形体与秦国日益强盛的发展趋势不相匹配,特别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综合国力愈加壮大,法律条文的颁布及向新征服领地的不断推广,普通百姓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文字的使用频率。经济和社会快速的发展必然导致当时文字书写上的变革,以适应教育的普及和法律条文的抄写宣传。
商鞅变法(参2)
在这种大背景下,大篆被隶书慢慢取代就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
隶书具有书写便捷、结构简单、笔画平直等特点,当然会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
隶书
关于“隶书”这一名称也比较有争议,传说认为“隶书”得名于程邈的官职。程邈为秦代书法家,做过"胥吏",是"隶"中掌管文书的芝麻小官,他创制了这种书体,故称"隶书"。后来,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而入狱,入狱之后他整理了3000个字禀奏给秦始皇,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因此赦免了他的罪行,而且还封他为御史。当然,这只是关于"隶书"的传说,隶书的产生和出现绝非他一人的功劳,他可能在整理和定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这样说隶书: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
《汉书艺文志》中说:"秦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序》中也有记载:"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
由此可知,隶书被广泛采用就是因为其形体便于书写记录。从文献和命名来看,"隶书"最初的来源应是当时社会底层人所使用的书体,官府及其他上层统治者则以篆书为书写形体。古时把沦为奴隶和从事繁重劳役的人称为"隶人",地位低下者也以此称之。这种书写形体广泛使用于社会下层,称之为"隶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隶书的出现和广泛流行堪称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
与"变隶"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件汉字变革事件则是近代的汉字简化。汉字简化与"变隶"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其变革的方式和途径则是天壤之别。隶变是潜移默化,由下及上,以民间固有的形体变革推动整个汉字书写体系的变化,这是一个逐步完成的工作。简化则显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采取了由上及下的行政推广模式,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大批汉字的形体构造变革。当然,二者变革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变隶" 的重要工作在于变圆转笔画为平直笔画,把象形笔画化,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书写形体。简化则是对汉字笔画的缩减,对书写形体没有影响。可以说,"变隶"是大众的功劳,简化是专家的功劳。
汉字简化工作开展时招募不少语言文字专家,这些专家为简化汉字下了不少功夫,搜罗文献,对比古文字形体,确立字形。他们从居延汉简里找到了简化了的"车",从金文中找到了笔画较少的"万",从草书中找到了"书"。
繁体字与简体字
汉字简化工作意义重大,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为后来扫盲和义务教育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汉字简化作为短时间完成内的工作难免出现问题,一直为大家诟病的"爱无心"、"亲不见"就是典型的例子。汉字简化至二简就踩了急刹车,也阻止了汉字朝着"胡乱简化"的方向发展。
二简字表
目前我国仍是简繁并存的局面,港澳台仍使用繁体字,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一国两字"的局面恐将长期共存下去。
参考文献:
1.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 2009.03。
2.杨新华,钟银珍编,《商鞅变法》,金盾出版社 , 2002.07。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开展“三八”女神节形体礼仪培训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厅堂员工的职业素养,展示厅堂员工良好的精神面貌,3月10日上午,兴业银行济南分行下辖烟台分行开展了“三八”女神节形体礼仪培训活动,近30名女性员工参与其中。
此次培训特邀请到专业的形体仪态导师,老师从如何“站”得得体、“走”得自信、“坐”得优雅、“指引”得大方为切入点,细致指点女性职工站立仪态、行走步态、落座、起身、等候指引手势等日常礼仪。培训中,女职工们还跟随节奏明快的音乐进行了颈、肩、手、腿等部位的练习,时而笔直站立、时而舒缓抖肩、时而优雅扭腰,充分展现了兴业银行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动人风采。活动现场,老师还针对职场女性长期伏案造成的体态不佳的情况,系统讲解了如何纠正脖子前倾、骨盆前倾等不良体态的方法,让身体正确归位,还女性职工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该行厅堂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不仅帮助女性员工塑造了优美的体态,提升职业礼仪素养与形象,同时帮助女性员工放松了心情,疏导了压力,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女性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下一步,兴业银行烟台分行将加大对厅堂女性员工的关心关爱,及时解决女性员工工作和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大家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董卿 通讯员 杨婵玉)
有关“现代性”的图景,从一开始就有偶然成分
20世纪,属于过去。
24年前的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都在告别1999年,等待新世纪的到来。转眼间,我们即将站住21世纪的第25个年头的开端。
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世纪能像20世纪那样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诸如民族国家、战争、“大萧条”、市场经济、全球化,每个关键词都是一部沉重的变革历史,在这其中,现代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这个地球上铺开。
重访20世纪的学者向来是不少的,但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有此尝试的,却是稀缺的。既然是“重访”,自然就不包括20世纪的社会学家对所处年代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当下的20世纪,而不是作为重访对象的20世纪。社会学专于分析结构、机制,而有关历史和时间的研究则一般被划为历史社会学范畴,成为一种专门的领域。这在社会学奠基者——如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历史本是社会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这是两位历史社会学家(很遗憾不得不强调“历史社会学”)的对谈。或许,我们不必去纠结究竟是称呼他们为历史社会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当今社会学界比较具备历史视野的学者,其视野和见解如何,得让方家来评判。
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曼。他四卷本的 《社会权力的来源》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学界有人认为他是我们年代最接近韦伯的人物,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韦伯。当对谈人约翰·A.霍尔问起他关于现代性的定义时,他尽管说“我并不确定这个词的其他意思,我更倾向于不试图定义它”,不过也表示了对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阐释。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他在与霍尔的对谈中继续使用了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四种权力来源)概念表述其看法。他认为,有关“现代性”的图景,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偶然性。
原文作者|[英]迈克尔·曼
《21世纪的权力:与约翰·A.霍尔的对话》,[英]迈克尔·曼著,陈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3年11月。
战争的理性与非理性
约翰·A.霍尔: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喜欢运用现代性的概念,因为某种程度上偶然性从一开始就是图景中的一部分,尤其是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20世纪的特点是巨大的偶然性变迁。当时主要的危机是什么?
迈克尔·曼:有两种危机。第一是重大战争,战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具破坏性,并且它们源自一个将发动战争常态化的环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和欧洲曾爆发过的大多数战争如出一辙。它与海外帝国无关,而涉及在欧洲,强国援助其庇护国。
约翰·A.霍尔:所以这关乎权力的平衡。
迈克尔·曼:是,这是传统的战争。
约翰·A.霍尔:为何它变得无法控制?
《帕斯尚尔战役》(Passchendaele,2008)剧照。
迈克尔·曼:你是指为什么他们打了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这个问题值得详述,因为其涉及的过程就当时的主要战争危机而言颇为典型,这在两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中也有类似之处。他们是出于某些不理智的原因,这并不是一种传统的因果解释。大多数的解释都具有十分强大的理性元素。而我的解释是,战争是外交的默认模式。正常的外交努力失败之后,战争就成为可接受的选择。
欧洲在1914年走向战争的实际过程是颇为复杂的,其中涉及的不止一系列偶然性。刺杀大公是真正的偶然。塞尔维亚阴谋者的刺杀行动本来已经失败了,但大公的车迷路了,它慢慢地经过一家咖啡馆,闷闷不乐的准刺客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正在吃着一块三明治。普林西普敏捷地抓住了他的第二次机会,刺杀了大公及其妻子。奥地利坚定不移要惩罚塞尔维亚。奥地利法庭以大多数票通过,奥地利必须战斗以维持其地位。讽刺的是,大公的死亡意味着主和派失去其领导人。这样的论点最后胜出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战斗,那么别人也会利用我们。”但战争也可能针对俄国,它迄今还是塞尔维亚的保护者。
奥地利被德国政府所支持,受其军事支持。事实上,德国政府已决定,一旦开战,它不仅会东进攻击俄国,还会西进攻击比利时和法国。这更令人困惑,显然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如果德国希望寻找“阳光下的土地”,那它显然也在和平地实现愿望。当时它正在工业、经济上慢慢赶超英国,并且在大陆逐渐获得霸权。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将海外殖民地留给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已没那么有利可图,虽然白人自治领和印度是例外,但反正德国也得不到它们。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德国领导人没那么有耐心,反而用战争取而代之。他们选择战争,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英国会加入战斗,英国也没给他们明确的信号表示自己会加入战斗。英国当时是自由党政府,如果有战争的危险,自由党内阁的三分之一会辞职。这样就会有选举,分裂的自由党很可能会失败。
《鸟鸣》(Birdsong,2012)剧照。
外交失利,武装力量动员开始了,这可能是防守的姿态,一旦战争爆发可以保护自己。但动员有时候会呈现出挑衅的形式。对德国而言,要动员武装力量,实际上就包括要占领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军事车站。比利时与英法签订了协定,如果它遭受攻击,英法会前来援助。当时有的德国人没预料到英国会加入,有的德国人预料到了,但低估了英国的力量和决心。英国的力量远在天边,但它的力量是全球性的,他们没看到这点,或没预料到英国会运用皇家海军的封锁力量,并且英国(和法国)会运用殖民地和白人自治领百余万的军力。许多人听信了英国“爱好和平”的自由党修辞,他们以为英国不会真有战争乃至鏖战的胃口。因此他们高估了自己的机会。俄国人……好吧,我也可以这样继续说下去。但我的点在于,强国间不能测量到彼此的反应,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权力型构,部分是因为国内的动机缠上了地缘政治的动机。
在此当中,地缘政治的特定逻辑在发挥作用,但会夹杂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逻辑,偶然性也会加入其中。但面对这些困难,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对战争的准备,相关的情感也被考虑进来——不要丢脸,不要放弃,到最后就成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展现出我们的勇气”。就像是在操场上打架的小男孩,他们必须展现出自己的男子气概。还有另一种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在大多数战争中,每一方都认为自己会胜利,这是战争最基础的非理性,但这是不可能的。有一半国家会失败。
《至暗时刻》(Darkest Hour,2017)剧照。
重访20世纪那场
西方世界“大萧条”
约翰·A.霍尔:我们会忘记萧条和衰退平息的时候。萧条和衰退可不仅是循环性的。1919年后,在某些地方要恢复正常是颇为困难的。事实上,纵观20世纪20年代,没几个国家的经济是蓬勃发展的。但这导致了“大萧条”——最主要的经济危机之一。你可以多谈谈“大萧条”吗?什么导致了“大萧条”?
迈克尔·曼:我会首先解释其在美国的发展,美国是最受影响的经济体。一系列打击累积起来,导致普通的衰退走向“大萧条”。我们必须记住, 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一直都并不十分兴旺,大众消费也并不高。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过度生产带来了全球的农业衰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结果。在美国,衰退在1928年蔓延到建筑业和生产业。
1929年10月24日,纽约《布鲁克林每日鹰报》(Brooklyn Daily Eagle)头版,“华尔街在恐慌中崩溃”。
与此同时,投资者似乎对被大力吹捧的营利技术表现出过高的信心,股票市场泡沫随之出现。过度的投资、萧条的生产结合起来,导致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破产、银行倒闭和失业。信贷枯竭,消费骤降。政府和美联储的回应是紧缩通货,并限制货币供给。这正符合经济学的正统看法,政府的角色只是帮助处理股票价值清算、不营利的商业、过剩的工人和过高的工资——直到市场的力量重建均衡。但事情并没这样发展。事实上,这样的紧缩通货将日渐严重的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通过金本位制,美国的问题被传导到已经摇摇欲坠的世界经济。固定汇率将美国在价格和利润下降方面所受的冲击传导到其他经济体。美国的国际贷款也同样下降了,这削减了外国人通过出口支付此前贷款的能力。他们觉得他们也需要限制信贷、提高利率,这意味着他们也在衰退时紧缩通货。
这是金融机制的后果,这机制正是由现代经济学家建造的。他们反复争辩不同冲击的权重。他们并没能很好地解释,这场打破旧纪录的萧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要做到这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解释扩展到工业结构、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中——更普遍地,扩展到社会权力的来源上,因为这是更为普遍的危机。
《奔腾年代》(Seabiscuit,2003)剧照。
简而言之,权力关系的四种结构转型正在拉开序幕。首先,农业是经济体的传统砥柱,由于全球生产过剩,它在走向下滑、萧条。它的剧痛极大促成了“大萧条”。其次,工业正从剧烈的技术变革中转型,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工业转向轻工业成分更大、消费者取向的制造业。然而两者结合并不能承担充分就业经济的重负。
旧工业不再扩张了,新的工业仍然弱小。科技也没能不负众望。再次,旧制度的上流阶层仍控制着世界的金融,他们试图通过“清算主义”(liquidationism)意识形态和金本位维持自己的霸权,这只让情况更糟。这些不仅仅是“错误”。这是在阶级权力和道德系统上的最后防卫。相反地,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在寻找更完善的社会公民身份,而直到“大萧条”导致其政治同盟的衰败(这也只是某些国家的情况),他们才有权力去挑战这一正统。最后,地缘经济权力从英国霸权、强国协调政策的状态发生转型。但当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替代性国际制度。既没有霸权,强国间也没有稳定的合作,它们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和约所带来的冲突切割得四分五裂。
如果我们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发生了什么,这种对“大萧条”的结构化的探寻方法会得到更多佐证——比起战后兴起的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萧条”也不见得更奇特。大繁荣体现了四种转型的日渐成熟: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迁移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了劳动力;大众消费社会崭露形体,并与高消费需求相关联;在生活福利方面的普遍社会公民身份、累进税制、保证完全就业和高工资的政策都已制度化;美国这个新的霸权国为国际经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规则。当然,这一对照显示出,经济永远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力来源交缠,无论时代好坏。
21世纪的问题
约翰·A.霍尔:你一开始提到了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中,金融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否使得2007—2008年的危机迥然有别于“大萧条”?
迈克尔·曼:其中有同有异。它们都由金融危机促成,先是信贷危机,后被债务危机恶化。它们都处于一个日渐不平等、大众收入下降的时期,它们都发生在科技创新无法带来更多增长之后。尽管现在的金融服务业比起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要更为庞大,但它们在当时是统治阶级“旧制度”的核心,政治经济随他们的需要而剪裁。我已指出,政府将自身绑在金本位上,以向投资者证明其经济的“资金充实”。在两次危机中金融投机者都被稳住了。
但是没错,今天的债务水平要高于“大萧条”时期。
纪录片《恐慌:2008金融危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Panic: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2018)。
全球失衡的问题使得债台高筑,却似乎也提供了通过债务解决收入下降的简单手段,“大萧条”时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可见的金本位束缚则变成了更不可见的美元浮动和跨国资本的束缚。“大萧条”前并没有多少监管存在,然而眼下这场衰退发生在大量管制后的去管制中。20世纪30年代的回应是更强大的国内管制和以邻为壑的贬值政策,并在国际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在今天,国际和国内管制能实现更好的平衡。不同点在于,今天的大多数国家都历经了这样的一段漫长时光:国家更频繁涉足经济生活,重视工业多于金融业,重视失业率多于通胀,重视凯恩斯主义多于新古典经济学,并且还存在殷实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近来试图与之抗衡,它已有所进展,特别是在英语国家。
但是政治经济学上仍存在许多变种,其丰富程度远胜于在那些曾受“大萧条”波及的国家之中的情形。或许之前在谈及目前的危机时,我对这些变种没加以足够强调。北欧国家以及那些更大更稳健的欧洲经济体(如德法)在面对投机时,在本质上就没英国和其他南欧国家那么脆弱——因为同处欧元区这一独特性,他们乍一看似乎同处一艘脆弱沉船上。日本、印度和中国也没那么脆弱。澳大利亚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加拿大受益于对金融部门的严格管制,美国则受益于拥有世界储备货币。虽然现在全球化更猛烈,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国家的变化亦更为丰富,这再次说明全球化是涉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21世纪的权力:与约翰·A.霍尔的对话》。
原文作者/[英]迈克尔·曼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