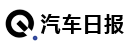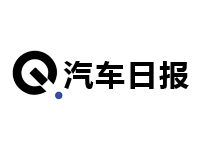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星期球赛”:抗战时期的贵阳“村超”
1924年,贵州“桐梓系”军阀资助了一支由九名学生组成的体育代表队,代表黔省参加在武昌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全运会期间,贵州队仅参加了篮球比赛,但首战便以3∶97的巨大差距败给了马尼拉华侨代表队。(Aandrew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s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79.)这个略显“悲壮”的故事反映出民初黔人体育基础的薄弱,但这些青年学子或许意想不到,多年之后,一股热烈的体育浪潮将席卷他们封闭的家乡。
业余球赛的兴起
作为西南四大公路(湘黔、川黔、滇黔、黔桂)的交汇点,抗战时期的贵阳一跃成为后方重镇,大批外来机关、学校、企业纷纷迁入这座曾经籍籍无名的西南边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随着外来职员和学生群体的增多,体育文化也逐渐活跃起来。电政管理局的一位吴姓职员回忆起他初到贵阳时的业余生活仍旧历历在目:
我1939年8月来贵阳时,正值年轻力壮,要求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身体,所以常去民教馆玩篮球。由于人地陌生,只和一些青少年同玩……当时练球的方式是:三个人一组,同攻一个篮。五个球一轮回,输者下,赢者坐庄。我在他们当中年龄较长,已参加了工作,经常请他们吃“甜酒粑”,可以说是“球朋友”,所以我和他们相处的气氛非常融洽。
如其所述,职员和学生群体以青壮年居多,或多或少都在新式学校接受过体育教育,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普遍较高。因此,各机关、学校及企业通常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类球赛。1938年的盛夏,贵阳私立毅成中学组织了篮球、排球、乒乓球锦标赛,校长与教员打造奖杯两个,学生自治会也制作锦旗六面,以资鼓励。对于当时只有两百余人的毅成中学而言,这样的排场可谓隆重,因此特意登报宣传。类似的业余球赛有时在单位内部进行,有时由某一单位发起,众多单位组队参与。
尽管总是被赋予“提倡国民体育”的宏大意义,但彼时业余球赛更现实的价值在于弥补大众的娱乐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身处异乡的“下江来客”(当时西南地区把江浙沪一带的移民称为“下江人”。)而言,各式各样的体育竞赛为他们枯燥的战时生活增添了不少活力。多年之后,一位曾疏散至贵阳的东北中学校友仍清晰记得当年他和同学们对于业余篮球赛的痴迷:
东北中学酷爱篮球运动,大部分同学在贵阳集中后,虽然篮球队的两名绝对主力还没有到达,现有的几名队员,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于牛刀小试了,可惜赛了两场球全都败北,铩羽而归,到场看球的同学们也很泄气,大家天天都在盼望那两名球员早日到来,甚至每天都有人到汽车站去等……后来这二位篮球健将终于搭上便车来到贵阳了,同学们都很兴奋,几天后便在篮球场约了几场比赛,有输有赢,不再是每场败北了。
年深日久,这些球赛以何种名义发起?当年的亲历者可能早已遗忘,或许这对他们而言本来也不重要,但过去伙伴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如何、心情怎样却记忆犹新。换言之,体育竞赛给予当事者最切身的经验是“娱乐”而非其他。恰如法国文化史家乔治·维嘉雷洛(Georges Vigarello)所言:体育其实被当成了一种“劳动补偿”,有助于将大众从日常紧张的节奏中解脱出来,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恢复和运用体力。
“星期球赛”的诞生
内迁群体的到来不仅使贵阳的业余球赛变得活跃,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球类运动的“技艺革命”。以大众最为喜爱的篮球为例,尽管篮球运动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贵州,但到抗战前夕本省球员的技术依旧十分落后,不少人采用“作揖式”的原地抱投,能单手投篮、跑动投篮者甚少。并且战术也很“原始”,“死前锋、死后卫,锋不卫、卫不攻”的状况普遍存在。因此,当外来职员和学生在贵阳球坛上初露头角后,他们所展示的绝招,如急性跳投、运动单手托篮、变向变速、快速突破、隐蔽传球等,立即令贵阳人大开眼界。同时,以往攻守截然分开的单纯攻防战术也被“五攻五守”的集体战术所取代。随着赛事的频繁举行,新技术和新战术得到广泛传播。
球技的提升和战术的更新让业余球员的表演更加精彩,同时也更具观赏性,每逢开赛总有不少普通市民驻足观战,而这种吸引力逐渐衍生出了“商业”价值。老贵阳人最为熟悉的体育赛事当属“星期球赛”,它由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省立民众教育馆以及贵阳《中央日报》社共同发起,主要事务交民教馆办理。星期球赛将分散在各个单位的业余球队聚集到一起,每周末定期举行二至三场比赛,地点就在民教馆球场。起初只有篮球赛,后增加了排球赛、小足球赛,这项活动一直从1939年持续到“文革”前夕。
星期球赛自开赛之日起,就显现出了半商业化球类联赛的特征。之所以给予它这样的定义,主要源于其“营利性”,几乎每场比赛观众都需要购买门票。1939年球赛门票价格为0.05元、1941年为0.2元,1943年则涨至2元。虽然票价逐年上调,但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看球始终是贵阳较为廉价的娱乐活动。便宜的门票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对篮球运动的追捧,保证了星期球赛的收入。1939年3月19日,由防空学校对阵特务团的首场球赛就吸引了近千名观众,门票收入45.1元。到当年5月,这个数字已突破千元。可见,这项创造性的赛事一经推出便获得了成功。球赛原则上能够支配部分运作费用,其余部分上缴国家,《中央日报》负责向大众公布收支。不过,这种自我监督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球赛收入状况愈来愈缺乏透明度。
门票收入的增长反映了贵阳民众对星期球赛的狂热,它既为体育爱好者搭建了操练、切磋的舞台,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感官盛宴,星期日“看球”在战时的贵阳成为了一种新的休闲时尚。频繁的赛事还催生了球迷群体,每逢自己追捧的球队登场,部分球迷便提前到人来人往的电影院打出助威广告,有时还会购买水果、点心、电影票、洗澡券甚至备下酒席慰劳球员。与此同时,主办方也通过各种噱头刺激大众的观看欲望,比如邀请明星或外埠强队参战。1942年6月,有“电影皇帝”之称的金焰受邀参加了一场比赛,众多青年男女慕名前来一睹其风采,报纸用“盛况空前”来描绘当天的场景;同年8月,陪都“常胜军”黑队篮球队远征贵阳,迎战本地强队辎校队,由于观众数量过多,竟然压塌了球场的木质看台。此后,贵州裕民盐业公司经理刘熙乙将木质看台改造为石级看台,并以其父之名将球场命名为“维周篮球场”。可以说,星期球赛是一项两全其美的创造,它既呼应了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国民体育运动,又将大众对体育的热爱化作了一笔笔可观的收益。
民国时期的维周篮球场以及来看球的人。(图片来源: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百年图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球赛中的“名”与“利”
正是由于球类运动(尤其是篮球和足球)对贵阳民众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筹办“义赛”也就成为部分机构和社团募捐的手段。募捐的名目可谓五花八门,或是慰劳前线将士、或是赈济外省灾民、或是募集教育基金,甚至捐献滑翔机。门票、义卖两项是募捐球赛的收入来源。为了博取观众眼球,主办方通常会邀请实力强劲的球队参赛,故而义赛的门票价格往往高于平时。1943年秋,在为中正中学筹募基金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因有著名的东方球队“参战”,门票一度卖到20元,是当年普通星期球赛门票价格的十倍;而1944年10月举办的“协济入黔文化人”篮球赛,门票价格定为50元,接近当时贵阳一位普通教员一个星期的收入;尽管如此,球场看台依旧高朋满座。球赛结束后,主办方还会以拍卖的形式出售比赛所用的球,即义卖。地方大员、富商名流在义卖场上“仗义疏财”是常有的事,例如,在1943年的“救灾球赛”闭幕式上,比赛所用的篮球竟破纪录地拍出了11500元的“天价”。对竞拍者而言,其竞逐的并非一个简单的体育用品,而是一种热心公益的象征性符号。
地方报纸关于一场“义赛”的报道。(图片来源:《贵州日报》1941年1月2日,第3版。)
为了鼓励大众慷慨解囊,报纸极力渲染募捐球赛所承载的宏大意义。例如,在1939年的“献寒衣”篮球赛前,报社的一位主笔精辟地写道:“今天的篮球赛是一个出钱出力的双簧好戏,观众出钱;球员出力,出钱的是为寒衣;出力的是为体育。捐献寒衣,是抗战的要功之一;提倡体育,是建国大计之一。这一出双簧戏,观众与球员合力拍出来的,是抗战建国。”不可否认,大部分义赛的发起饱含着家国情怀。但是,由于募捐球赛往往缺乏完善的财务监督机制,并且观众在体验完一场场体育狂欢之后也并不在乎自己贡献的善款流向何方,所以“公益”与“私利”之间的界限有时变得暧昧不清。1944年,黔省教育厅奉教育部之命发布了一则法规:
举行运动比赛,原系推行国民体育之一种有效方法,惟每以管理欠周,致有利用运动比赛或体育表演发售高额门票,籍以敛财情事,殊悖提倡运动比赛之本旨,嗣后应切实管制,并注意下列二点:(甲)凡发售门票之运动比赛或表演,应对其售款用途及票价,加以审核及限制。(乙)举行运动比赛,不得以现金作奖励,语等。
根据该法令推测,以体育之名、行敛财之实的现象在抗战末期可能已经十分普遍。尽管政府没有明确指出谁是“违规者”,但吊诡的是,自从该法令颁布之后,贵阳星期球赛一度免费向大众开放,而且形形色色的募捐球赛也大为减少。不过,国家对此现象的关注也从侧面反映出,体育竞赛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商机”。(孟浩:《边城欢哨:全面抗战时期贵阳的国民体育与公共生活》,《城市史研究》第43辑。)
如今,若不是资深球迷或者地道的“老贵阳”,或许很难找到隐匿于贵阳旧人民剧场旁边的篮球场。不过,当人们穿过蜿蜒的巷道和破败的车棚好不容易走进它的时候,或许也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狭小、简陋,四周还略显杂乱的场地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维周球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第五球场)。作为贵阳曾经热闹非凡的“体育中心”,这座镌刻着时代痕迹的篮球场见证了一段热辣滚烫的筑城体育史,一个个漂亮的传球、突破、跳投、上篮在这里化作永恒的记忆。尽管“星期球赛”早已成为掌故写入了地方史志,但黔人的体育精神和体育基因却得以延续,并不时被唤醒。
今天的维周篮球场(第五球场)。张义2023年拍摄。
成都老茶馆档案里的时代与家国
新华社成都5月9日电 题:成都老茶馆档案里的时代与家国
新华社记者吴光于
由国家档案局提名申报的“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5月8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该组档案收录了1903年到1949年期间,有关成都老茶馆日常经营、管理的珍贵原件,有手稿、图表、照片、印刷品等共计6345件,不仅全方位记录了近代成都老茶馆的活色生香,更反映出茶馆与城市的共生共融,以及茶馆文化滋养的人文精神。
小茶馆 大时代
“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中,既有茶馆经营的日常,如申请登记证和营业执照、租约合同;也有政府、行业协会的管理,如茶馆数量统计、售茶定价等。
成都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批档案见证了近代茶文化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全方位反映了老茶馆在休闲娱乐、信息交换、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的多元功能,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珍贵史料。
《成都通览》记载,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条,茶馆就有454家。档案中,1929年“四川省会警察局”的统计表显示,当时成都的茶馆已达641家。
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喝茶休闲(2021年6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成都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20世纪初期至上半叶,成都平原由农耕经济向商品经济逐步转型,档案反映出茶馆作为小商品经济的代表,在城市经济转型浪潮中稳步发展。
档案还显示,茶客人群来源广泛,既有民间艺人、小商小贩,也有外国领事官员,折射出茶馆的包容性。档案中还不乏保护女性在茶馆中的工作权益、保护女子经济独立、禁止骚扰女性的内容。
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曾对这批档案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据此完成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他认为,通过茶馆,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还能从背后的细节中重构大众的日常生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普通读者认识自我、关注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文化交流的平台 家国记忆的承载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有400多……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这段1949年的录音,是瑞典年轻人马悦然在成都春熙路一家茶馆里,对着一台钢丝录音机讲述的见闻。他的声音之外,茶馆里人声鼎沸,茶馆外车水马龙。
寄居成都的日子里,茶馆是马悦然捕捉方言韵律、观察市井生活的一扇窗。多年以后,他成为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耄耋之年,他仍对成都老茶馆念念不忘。
档案显示,茶馆里的文化交流非常兴旺,不仅为川剧、清音、皮影等传统地方剧提供了舞台,电影放映等“新式文化”也在此萌芽、发展。
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戏”搬上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人们在喝茶聊天休闲(2021年6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老茶馆还承载了商贸洽谈、重要活动举办、信息交流、社会纠纷调解等功能。档案记载,20世纪40年代,“工商业同业公会”曾在中兴茶园举行商业洽谈会。1918年,英国、法国领事馆、商务访华团曾在成都茶馆里举行茶会,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
其实,档案之外,还有很多在当时难被书写的茶馆故事。
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老板李强(右二)为茶客们添水(2021年11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成都双流区擦耳岩正街,一幢斑驳的老屋曾是一家茶馆。主人徐茂森明里和侄儿一起做生意,暗里为地下党员提供住宿,协助转运武器。这间茶馆里,徐茂森叔侄二人协助地下党员发动当地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农民翻身会”,还创办了地下刊物《火炬报》。1949年中秋前夕,联络站因叛徒出卖暴露。1949年12月7日深夜,叔侄二人与30多位革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桥畔英勇就义。20天后,成都解放。
茶馆文化 源远流长
成都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茶馆,每天凌晨4点多,老板李强就开始生火烧水,准备迎接风雨无阻的老哥们。老茶客中年纪最大的已经90多岁,在这儿喝了一辈子茶。老人们喝茶只需1元,价格多年不变。慕名而来“打卡”的游客喝茶则是10元,人们也觉得心甘情愿。
人们在成都太古里大慈寺内的茶社喝茶(2023年6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今天的成都,常住人口已突破2100万。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茶馆也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锦江畔的望江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院的树荫里……2万多家茶馆与城市脉搏共振,融入城市肌理。
“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成都高新区铁像寺水街的陈锦茶铺立于戏台边的两句话,传递着“天府之国”遇事不惊、从容不迫的人文精神。
在成都茶馆兴盛的100多年里,这种精神已自然地融入城市的骨血。无论周遭环境如何紧张忙碌,只要走进茶馆,端起茶碗,便如同坐上了一叶无形的扁舟,茶香氤氲中,便能从容地看山河大地,听鸟鸣猿啼,安稳、笃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