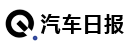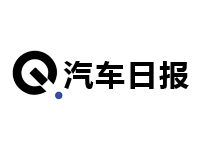刚刚申遗成功的“送王船”,是一种怎样的民俗?
陈花现
【按】2020年12月17日,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经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
从一场等待开始
2020年12月16日晚,我跟厦门的几个朋友在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里守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直播。当晚,在宣布到排在8B21的太极拳之前,便到了大会下班的时候,本以为人家会加一下班把今天的流程走完,但没成想,守了一夜,悬念就这么被强行留到了第二天。或许是太在意这个结果,当晚也没怎么睡着,就像期待着新番一样,恨不得赶紧把进度条拉到第二天的晚上。
12月17日晚八点半,大会终于开始了。8B21太极拳顺利通过了,紧接着,就是8B22“送王船”。那声清脆的锤子声响了起来,大家都举着手机,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但又都不敢发出声音,生怕错过任何信息、或打扰了彼此的录像。在大会进入下一个项目以后,刚刚为了拍视频强忍住的情绪,便释放出来了。鼓掌、欢呼、想着去哪庆祝一下。
随后,“送王船”这个看起来有些魔幻的词汇,开始在朋友圈里频繁出现。“太极拳”作为全民皆知的国术在历经12年的艰苦申遗后终于如愿成功,而“送王船”这一主要在东南沿海至东南亚所流行的华人民俗则激荡起了更多人的好奇。
从送瘟到送王的转变
“送王船”起源于我国古代民间的送彩船习俗,宋元时期就有相关科仪本《神霄遣瘟送船仪》的流传,虽藏于《道法会元》之中,但追其根本也是民间巫仪与道法的结合之成果。送船习俗原本以送瘟为目的,时间多在农历五月端午,或春夏之交疫厉作祟时节,明代两湖流域端午龙舟竞渡后把龙船烧化也有送瘟之意。海南省博物馆藏有《龙舟大神宝像图》一轴,其内容就是以都天元帅为领,用龙舟宝船押送瘟部众神等前去仙乡蓬莱。
清乾隆的《泉州府志·卷26·风俗·岁时》便记载了这么一场五月节送瘟船的仪式:“是月(五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诞道设醮,至其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
《龙舟大神宝像图》海南省博物馆藏
送船这个习俗所流行的地区,也多是依水而生,有船舶崇拜的区域,如长江流域及江浙、东南沿海等地,乃至随着民俗学调查的深入,我国许多内陆省份也保留有以船送瘟的仪式。但追其根源还是远古临水地区人群,对于舟楫的崇拜,把视野放到太平洋沿岸也能看到类似仪式,在日本长崎有“精灵流节”即为亡灵超度的放船仪式,韩国济州岛有施放稻草船的“灵登祭”。
而这种禳遣类型仪式,也被应用到航海之中,在明代漳州人张燮的航海笔记《东西洋考》中便有提到大船为祈求航海顺利,而施放彩船之举。明清以降,则在闽南沿海社区,结合民间的王爷信仰与海上贸易兴盛而产生的福船崇拜,演化成了多在秋季转东北季风以后,才举行的“送王船”。究其从送瘟船,转换到送王船的背景原因,一是医疗条件的日益改善、二是海上贸易带来的红利让民间信仰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其仪式意义从原始的驱疫送瘟,演变成了上礼天地、朝天求忏以顺风得利,下普施孤魂,纪念航海、战乱期间遇难孤魂的综合性醮仪,称之“王醮”,民间俗称“贡王”或者“请王”“送王”等等。
厉祭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醮的本意为祭酒之仪,后引申为礼敬天地沟通神明的祭仪。
民间信仰的根本动机无非就是趋吉与避凶,在“王醮”里趋吉的仪式由朝忏祈福来负责,而避凶则靠送船、普度一类的“厉祭”。对于“厉”这个名词,多数人有点陌生,但说到“厉害”这个词的词源,便是来源于古人对“厉”的看法。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从《春秋》子产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人的灵魂观念:其实“鬼”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归属感四处捣乱的“厉”。没有后代祭祀的都可以归之为“厉”,进而秦汉时便有厉祭之仪,以安抚两类灵魂:一是对时代有贡献但无后人祭祀;二是天灾人祸之中无所归属的。但从现在健康角度来看,没有得到安葬的尸骸确实会带来传染病,所以厉祭的内核之中还是有些朴素的卫生观念所在。但回归精神本源,通过祭祀达到可知的“归”,其根本还是出于对“未知与不定性”的恐惧。特别是像在东南沿海这种,需要在风浪中讨生活,没有足够且稳定的耕地地域,便希望通过厉祭得到一定的心理安抚。
从这种群众心理出发,春秋时管仲还创造性地将厉祭作为振兴经济提高税收的手段之一,让“礼”与“利”相通,通过“收民之牲”,通过祭祀推动民间消费,带动了所在地区“鱼市”的兴旺。但到汉以后在儒生的反对下,厉祭被视为不符合礼法的淫祀被加以打压,直到明代朱元璋洪武改制,鼓励民间祭祀以后,厉祭又重新回到民间祭祀范畴,而闽南沿海著名的王爷庙例如泉州富美宫、同安马巷元威殿、南安檺林庙三王府、南安寮洋灵应堂三王府等,也多是在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所建。
而在王醮进行期间的普度,则是传统厉祭下沉式传播的结果,乡间枉死无祀的孤魂在亦在此仪式里得以饱餐,最后跟着王船同赴仙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还活着的人对未知生命经验的不确定性。
王爷Ong-Ya
请来王爷因为迎来送往的代巡身份,多为彩扎金身 刘家豪/摄
既然送王船是由从早期的送瘟习俗演变而来,有些地方的民俗学家就偏执地认为王爷是瘟神。其实王爷的角色在闽南已经演变为押送瘟神疫厉的代天巡狩之神,甚至在闽南乡社间流传有王爷自服上天用来减人口的瘟药,为民而舍身的传说。古人对神的品质要求就只有核心的两点——聪明、正直,因为巡狩之职,百姓对于王爷的要求,就是要特别正直,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毕竟在大家精神世界的期待里,幽律定是要比人间的法律更严苛,以至王爷的角色常是由历史传说里最刚正不阿的人来担任,其中多为为国献身的忠烈,这也是民间情绪里对于公平正义最直观的追求。这也是古俗中厉祭的时代演化。
海沧钟山水美宫日常所供奉的没有形象王爷神位
王爷在民间使用的是巡回监察制度,也就是古代的巡按制,在明末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卷一·文臣》中有载:“代天巡狩,赞称巡按”。所以在闽南沿海的民俗中,便有“迎王、送王”之说,此迎来送往的时间,大抵也是符合民间祭仪“春祈秋报”的习惯。乃至因为代巡制度有些社区每科迎来的王爷姓氏、性格都不一样,在王爷到社区驻驾期间,会设立一个临时行馆,行馆里皂快隶三班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巡回法庭,放告牌一出,便接受阴阳之间的申述,人鬼间的冤屈常在这个临时法庭里上演,凭王爷之威信,促进纠纷的决断与和解。我们常言民俗是群体精神的行为映射也就体现在这里了。
而王爷的系统也根据区域习惯,有所不同,有单姓的、亦有三王府、四王府、五王府等不同的规格,在漳州地区的王爷行馆里,于王爷两侧还会配置一套天仙,这些天仙脱胎于传统的遣瘟醮仪,亦是帮助王爷收拾疫厉的。
在王爷完成巡回法庭工作以后,乡里合境便得恭送御史回朝复命,于是引申出了“送王”仪式,“送王”的方式会根据各地所延续的民俗传统有所不同,这也受所在地区的传统交通方式所影响,乃至有些地区有以纸轿送王的形式。但多数沿水社区,特别是以前有重要港口的社区,还是以船的形式来送王。毕竟船对于要靠一波碧水生活下去的群众来说,太重要了。
漳州港尾梅市的王爷行馆早朝 阮海松/摄
王船Ong-Chun
1919年 马六甲的王船
福船,是沿海居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历史上它是开辟海疆的座驾,糖茶换米的土货贸易,为缺少耕地的福建人带来粮食,更为他们输入缓解后来区域饥荒的地瓜,也承载着他们纵横东西洋的航道。现在的福建人多为闽越人与中原汉人的结合,在他们的文化血脉里也继承着闽越人对于船的精神崇拜。船是闽越人最紧密的生产工具,而他们也相信他们的生命走向终点后,船能够把他们运载到仙乡去,以致于我们现在在武夷山能够看到船棺的留存。而为王爷、王醮所拥有的福船,便被称为“王船”。
福船样式
19世纪末厦门港的中式帆船
王船的筹备与建造过程,其实是社群之间,一次水上生活经验的系统传递。王船开造前,须得择一清净的地方作为船厂,并立厂官像以做督工,建造期间为了确保船只的神圣性闲杂人等不得进入,但在这神圣性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是维护王船建造过程中的生产安全。然后就是选龙骨、钉船、造帆、立桅、落锚一系列程序的执行,在比较严格的社里,在执行这些流程的时间都要经过挑选,放在现在木船帆影已远走的时代甚是难得。一艘王船的建造多需经过2-3个月的时间,工匠吃住都在工棚里,社区耆老也会凭借自己的经验对王船的形制进行调整。
龙海港尾 督造王船建造与管理水手的厂官爷
王船亦较一般福船更为华丽,毕竟是精神的装点。王船船首为狮头象征辟邪,船尾的盘龙则为旧时官船的象征,船中为官厅,为王爷的指挥中枢,船后是排兵的将台插着象征五营兵马的五色旗,以及祭祀海神天妃的地方。船首两侧为朝天而看的龙目,船尾两侧为传说是海蛇或者海鳗的极鳅。闽越人视船为有灵性木龙,船尾两侧的极鳅实则是闽越原始蛇图腾的崇拜,也被视作福船的守护神,相传其舍身堵住了船舱的破洞,保住了一船人的性命。而船上多彩的旗帜,则象征的是以六方六兽、二十八星宿为系统的星斗定位。
漳州进发宫的王船及“做王船头”的九龙江上游道士
其实福船的形制,在历史上也经过了一个多元融合的过程,阿拉伯海船尖底海船的传入及水密隔舱技术的运用使得这类型船只,自宋元起便纵横于海上,广泛应用于福建人的军事、贸易、渔采之中。在木帆船失落以后,漳州的造船工匠有些早已转行,有些则靠着修补船只、钉造龙舟来延续自己的事业,而各社王船的建造,也为传统的造船师傅带来了祖辈经验的施展空间。而在造船期间,社里民众也要为王船准备一应的生活用具,蓑衣、斗笠、畚斗、扫帚、锅碗瓢盆、修船工具一应俱全,还有柴米油盐酱醋等日常物资,被称之为添载。
2020年10月12日,厦门厦港龙珠殿钉制王船
而王船要出航前的“做王船头”仪式,则是旧时福船出港程序的演绎,道士船上草鞋,点上船上众人,生动地模仿起锚升帆等动作,让大船驶出海港。
“船主、裁副、香公、舵工、直库、火长、大察、二察、押工、头仟、二仟、三仟、阿班、杉板工、头锭、二锭、总铺,合船伙计齐到未?到了。”(乾隆已丑年(1769年)季冬谷旦所敬抄的《送彩科仪》)我们可以从250年前的科本窥见当时的福船出航的面貌。
马六甲1933年送王船的采莲手,海沧钟山水美宫2020年送王船的采莲手(摄影 陈沧山)
王船送出港前的最后一段路,就是巡境游香,如果是送瘟船含义更大的地区,这段路乡社里的居民们是不能跟随的,并且都得关门闭户,用鞭炮把船炸走。而王船的巡游则不同,由村庄妇女扫路开道,乡里青壮尽出扛着巨大的王船在人浪上巡游,亦可增加村庄的团结度,所过之处沿路收摄邪秽,古俗还有水手吟唱采莲歌。以前的疫厉多是由不良的卫生情况引起的,而王船的出游则可以信仰的名义发动起全社里一起来大清洁,并借由鞭炮中的硫磺与热力进行消杀,这种狂欢氛围也能提振乡民们心气,在那个平时没什么东西吃的年代,亦多了一个聚餐吃肉的理由。
庙宇是精神的纪念碑,仪式是记忆的重演
2018年12月4日,与马来西亚马六甲怡力勇全殿结成兄弟宫庙
我曾有幸跟随参与此次申报的社群之一 ——漳州九龙江进发宫一同去参访马六甲勇全殿,当时我和这些世代生活在船上、皮肤被江上的阳光浸得发红的船民阿伯们头一次出国,到了机场需要出关,因为语言问题,不免被马方边检叫去办公室进行更加详细的登记,坐在工作格里的一个马来男人,指着办公室的方向,向我们这群人用闽南语喊着“去办公室!”顿时觉得多少有点亲切,但这种闽南语“服务”,却映射着生活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筚路蓝缕。
马来西亚马六甲福建会馆的妈祖像
勇全殿池王诞辰分驻到信徒家中的小型香火神像
在明清政权的更迭下,海开了又禁,禁了又开,沿海的海商集团以故国的名义延续着自己的贸易航线,也有思念故国的义士逃到了南洋,在南洋落地以期复国后能够再返回故土,这就造就了较早一批前往南洋的华侨,以致于到现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道士做醮的榜文一开头便是“……大中国 华省各乡里社合众善信人等现在南洋 马来西亚……”当初从故土来到番边,除了行李以外就是一包从家乡带来的香火,等到生活安稳,社群集聚,香火便成了庙堂,而庙堂也成为了华人社群的庇护所,成为了离乡时从家里米缸带出的那捧以解水土不服的米。这也是故乡精神走向海外延伸。此次入遗的马来西亚方代表宫庙——马六甲怡力勇全殿的池府王爷香火便是来源于厦门同安马巷的元威殿,正是由当时下南洋的同安人所带去。而马六甲曾经的送王船仪式中,亦有从厦门曾厝垵请过道士与三坛到南洋演法。
榜文
三千公里之隔的九龙江上,曾经遍布的水上社区,如今仅剩在漳州江滨公园旧烧灰巷路头旁停泊着的进发宫庙船,及少数以前烧灰巷船社的连家船。在漳州船民落实上岸政策的时候,世代守护进发宫庙船的老郑家十兄弟,依旧坚持要留住庙船,保持旧时船社的精神象征。每到台风季,他们多得到大船上守着,生怕猛涨的江水把船冲走,每年三月初三、九月十三几个船社的神诞节庆日子,原本船社的船民就会聚集到这里,一如以往地把愿望、忧愁、喜悦倾注到这里。
漳州进发宫在船上与码头上的送王船仪式(刘家豪摄)
旧时天灾与劳作的凶险,是我们现在所难想象的,船难、水灾、疾病的肆虐,让每条生命的留存都是庆幸,但那个过程对于信心的消耗也是确实存在的。而这种生命间互相怜悯与生命经验的传递,便通过仪式体现出来。亦通过“送王”这么一场盛大的醮会,使得社群通力协作,在世代的变革浪涌中,存续自己的文化能量。
送王船是远古巫仪、斋醮礼仪与民间精神狂欢的结合,这丰富多元的仪式,正是对应着旧时坎坷不断、悲喜交加的生活方式,而回归民间信仰的目的无非是趋吉避凶,从最早疫病的忧虑,到四处讨生活的艰险、乃至秋后丰收的喜悦,都浓缩在其中,狂欢能够为压抑多年的情绪打开缺口,就如同火焰即有光明也有重生,热烈过后,带来的是拼搏的勇气重生,而不是绚烂过后的虚无。
2020马六甲勇全殿的送王船
虽然在历史上,也多有儒生批判送王船这一极尽民间狂欢的仪式。但若是套用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理论却也得以解释。他认为民间的狂欢打破了平民大众日常“常规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对权威、权力、真理、教条、死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狂欢节则“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这是平民大众的世界,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性别的区分与界限”,是有“全民性、自由性和乌托邦的向往”。因为工作需要,必须游走在不同社里讨生活的船民,在历史上总是被视为流民,而为了能够完成工作,在船社里长辈对后辈的教育就是需要学会“吞忍”,这一情绪的压抑,在船社的送王船仪式里,得到了确实的释放,也给了他们再次面对生活的信心。
不论是离乡到南洋谋生的华人,还是九龙江边场域日渐限缩的船民,或者终日在浪涌之上讨生活的社群,他们所经历的压抑,是远离一线劳作,且作壁上观的历代批评家所难以体会的。因为他们不需要直接面对风浪,知识的壁垒可以让他们脱离凶险,以至于可以从容地追求山中的白云与圣人的训示。
从民俗到文化遗产
登录名录后马六甲怡力勇全殿的庆祝仪式
人类文化遗产名录最终强调的还是Living Heritage,活着的遗产,鲜活的文化生命体,远比一元起源观点的那种所谓的“最早”或者“世界级”更重要。所以特别强调社群与社区的连结与参与,此次中马两国的联合申报,也在大会当天,被称赞为经典案例。
此次送王船申遗的成功,其实是历史上沿海华人社区文化的共鸣,也是向海而生的先民们的精神遗存,但更是在文化上生生不息的传承结果。在与也让我们意识到民俗在当下时代对于我们的价值,更可以真正帮助到在人群与空间逐步萎缩的传统社区,增强面对大众时的文化自信。特别在马六甲的王舡游行,还能看到印度人、马来人等多种族人群的参与,给马来西亚华社文化的传承注入了巨大的信心。也让像漳州九龙江进发宫这样在城市化变革中快无岸停泊的船庙,创造些能够再延续下去的外在条件。
我们并不希望申遗沦为一场先到先得式的比赛,而应当是一场文化觉醒的开始,能够启发我们从世界的维度与人类的视野来看待自身的文化,让它真正成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产。在两地庆祝告一段落后,昨天上午,接到了勇全殿来的电话,大家都在感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会是更多!”
(作者简介:陈花现,闽南人,厦门闽南传统彩绘技艺传承人,日常致力于闽南在地民俗文化的探索与梳理,漳州九龙江进发宫疍民文化传习中心理事。)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