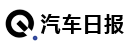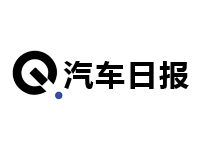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四围绿水绕重重,孤阁高撑渺渺中”,浅析画中的宋代水阁建筑
引言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宋代建筑在造型、构造和建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代稳定的社会和繁荣的经济,促进了各阶层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画家受到了各阶层的尊崇,名家辈出。两宋时期的画作,通常通过写实的手法,来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营造美好的意境,其中有大量作品对建筑及其环境进行了精细的描绘。
一、水阁环境特征宋代文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然仙境的设计格局,希望能够寄情山水,从山水之中获得情感共鸣。在水阁建筑的基址选择上,常将其立于山环水抱、树木丰盛的自然环境之中,水阁的布局顺应自然,保持原有的自然风貌特征,因地制宜。
在设计中,通过借景的方式,将自然山水与场地中的植物景观、建筑相互映衬,浑然一体,展现丰富的景观特征,从而表达水阁主人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趣。
古往今来,从原始社会时期对山石的敬畏之情,到封建社会时期文人雅士向往生活于山水之间,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石之上,中华民族对山石有着不同的感情。山体在水阁建筑营造中,不仅作为营建水阁位置的关键,同时也是水阁营建时的景观考量,通常会形成看与被看的景观需求。
《林泉高致》记载:“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
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通过山水营造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取向,择山而居,根据观景需求选择山体加以利用,利用自然山水进行构景,此时的水阁建筑便成为一种点景建筑。若有条件,文人士大夫会在自己的园林之中堆叠人工山体,凝练自然山体,保留其特征;或将自然山体进行写意化设计,形成假山或置石。
《水阁凭栏图》中山体作为远景而立,由高耸的主山和连绵的客山相组合,其他山体也按远近大小布置,山体与山体之间相互连接,形成“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的意境。此类宋画有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佚名《高阁观荷图》等。
二、水阁建筑环境的营建水体是宋代水阁建筑环境营建的重要元素之一,水体的运用,不仅充实了景观特征,而且营造出了自然的意境,充分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根据画作中水体面积的大小,以及其在画作中是否存在明显边界,将水体形态进行分类,主要分为湖、溪、瀑、池这四类,其中湖作为水体理水使用最为广泛。
以湖面为水体理水的主要特征是水面宽阔,在画作中与山体等景观没有明显的边界。在营造过程中,利用湖面,将人造景观与自然之景相结合,扩大了视野赏景范围,打破了人工营造的水阁与自然的界限,增加了观景人的联想。
《水阁凭栏图》所绘建筑之景亦是通过湖作为水体进行理水。《水阁凭栏图》的构图中,远景与近景之间都是开阔的湖面,与远处的山体相依相融,没有明显的界限。水阁立于湖面之上,湖中之水从平座底部穿过,湖水与驳岸相互连接,植物与水体相呼应,水体作为自然的过渡,将建筑周边营建之景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
山水体系是互为一体的,是写意山水园的基底。这个基底可以是城市园林的平地造园,经累土积石,人工营建;或者依景造园,依借自然的山、湖、溪、涧的变化地势造园,尤以文人园林为代表,妙于因借。
《水阁凭栏图》描写了江南之景,水阁立于湖中,水阁与岸通过廊道联通,水阁四面空阔,其形态在画中被完整地勾勒出来。水阁作为点景建筑,依借山水而造,将四周景色全部收入眼中,建筑和谐地融入自然山水之中。
《林泉高致》记载:“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
植物对环境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水阁建筑在环境营造时,通过人造植物景观借山之势、水之美而安居,将原本属于自然的“地利”条件在场地中构建出来。利用植被营造改变空间格局、重塑地形,创造舒适的微气候。植物与山水环境的结合可以加强或削弱地形起伏来塑造空间。
文人士大夫崇尚“修身养性”,这与《黄帝内经》中“养生”与“养心”辩证统一的养生观不谋而合。植物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含义能让人“寄情”,从而达到“养心”的目的。“寄情”的植物常见的有象征品质高洁的松、竹、柏、梅、兰、菊、荷花等。唐宋以后,植物逐渐成为文人的精神象征。
《水阁凭栏图》中,水阁两侧采用对植乔木的方式,其树种为柳树,柳树周围配置梅树,水阁对面驳岸是随意散植的水草和梅花,远处山石中遍植松树。对面驳岸散植的植物随意布置,三五一丛,呈现自然趣味,水阁两侧精心列植的柳树对称、整齐,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形态,增加了文人赏玩时的趣味。
三、水阁建筑特征宋代繁荣的经济为建筑营造提供了经济基础,随着一系列以文立国政策的推行,文人士大夫的地位有所提升,文人士大夫追求隐逸思想,希望在山水之间感悟人生,文人园林便成为他们精神审美物化的产物。
大量以游赏、宴饮雅集和感悟人生为目的的文人园林出现,园中水阁建筑作为文人士大夫居、观、行、游的场所,为园主提供了游赏、宴饮雅集和感悟人生的物质空间。水阁作为园中人为创造的部分,一方面代表着园主的审美追求,可供观赏;另一方面,它是园中环境构成的主要元素,是连接人与自然的重要纽带。
在宋画中,水阁建筑在画面中,将自然山水与园内景观虚实相隔,将其有机结合,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起到点景、隔景的作用。
宋画中出现的水阁建筑屋顶样式丰富,十字脊顶、歇山顶、悬山顶、攒尖顶等屋顶形式均有出现。歇山顶在宋画中为大部分水阁建筑所使用,如《水阁纳凉图》中的水阁建筑,其具有较为典型的宋代歇山建筑形象,如歇山顶垂脊均有戗脊,且山面较小。
悬山顶在水阁建筑中使用最为普遍,如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王诜的《莲塘泛舟图》等画作中的水阁均采用了悬山顶。攒尖顶建筑在水阁建筑中也有所应用,如佚名《荷亭消夏图》中的水阁采用了攒尖顶的样式。
十字脊顶是极其华丽的一种屋顶式样,这种屋顶形式是将两歇山顶,进行十字相交组合而形成的,极富有装饰性美感。十字脊顶在宋《营造法式》中未有记载,但是这种复杂的屋顶形式在两宋的画作中大量出现,等级较高的殿堂楼阁多采用十字脊顶的形式,如李嵩《水殿招凉图》。
宋代文人园林建筑布局不再一味地强调对称式布局,在文人园林的营造中,往往会依据自然山水进行建筑布局,宋画中这些建筑的组合,灵活多变,而建筑与建筑之间通常会通过长廊进行连接。通过长廊联系建筑,一方面可以解决文人园林出现在山水之中的高差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遮风避雨、遮阴纳凉,提供赏景之处。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
虽然人常说“遮风挡雨”,但相对于“雨”来说,居住环境对“风”的要求显然更加复杂,这一点在较为温暖潮湿的江南更为显著。相较北方,江南地区气候相对温暖,但对于水阁这类四面无墙的建筑而言,也不能一年四季保持开敞通风,因此拆卸灵活,则成为格子窗使用的一项基本要求。
相比于较难自由拆卸的棂子窗,槅扇自然是更好的选择,以便随四季气候变化,增减使用。宋画中水阁格子窗的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设置在檐柱间;设置在柱间矮墙上,形成阑槛钩窗;设置在擎檐柱之间,与上部横额、帘幕相结合。
结语《水阁凭栏图》中所描绘的水阁建筑,在环境和建筑营造上具有明显的江南地区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南宋文人园林的特征,其自然式的布局形态、适应气候调节的建筑营造方式等,充分体现了江南地区建筑营建特色。对比总结《水阁凭栏图》和其他宋画对于我们研究宋代水阁建筑环境和建筑营造具有极大的意义。
自然环境对于宋代文人园林中水阁建筑及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宋代文人崇尚山水的自然观将人工营造的环境与天然的山水环境有机融合,这样的山水观深刻地影响了建筑的选址与营建。将水阁建筑的宋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直观感受宋代营建文人建筑的生态观与自然观。
参考文献:[1]郭熙.《林泉高致》.
[2]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小景致,大意境——南宋刘松年小景山水鉴赏
刘松年 《雪溪举网图》 册页
明朝收藏家张丑诗云:“西湖风景松年写,秀色于今尚可餐;不似浣花图醉叟,数峰眉黛落齐纨。”说的就是刘松年的山水小景。
南宋刘松年画学李唐,画风笔精墨妙,山水画风格继承董源、巨然,清丽严谨,着色妍丽典雅,常画西湖,多写茂林修竹,在技法上刘松年变李唐的“斧劈皴”为小笔触的“刮铁皴”,山明水秀之西湖胜景;因题材多园林小景,人称“小景山水”。刘松年还兼精人物,所画人物神情生动,衣褶清劲,精妙入微。后人把他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为“南宋四大家”。
刘松年 《四景山水图》之春景
刘松年 《四景山水图》之夏景
刘松年 《四景山水图》之秋景
刘松年 《四景山水图》之冬景
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分四幅绘春、夏、秋、冬四景,每幅纵41.3厘米,横67.9至69.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四景山水图》描绘了幽居于山湖楼阁中的大夫闲逸的生活。全卷书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逸劲健。其中界画屋宇丝毫不爽,山石多用小斧劈破,可以看出与李唐的渊源关系,而秀润过之。
全卷画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逸劲健。其中界画屋宇丝毫不爽, 山石多用小斧劈皴,秀润过之。
春景,画堤边庄院。桃李争妍,嫩柳成荫,远山迷朦不清,杂树小草很有生机,给人以春意盎然、心情舒展的审美感受。堤头两侍者牵马携盒向小桥走近,阶下童仆忙于清理担具,像是随从主人倦游归来的样子。
夏景,画湖边之水阁凉庭。庭前点缀以湖石,四周花木丛生,水阁伸向湖中,扶衬以木桩梁架,有点像西湖十景中白堤上的“平湖秋月”。主人端坐中庭纳凉观景,旁有侍者伫立。
秋景,画老树经霜,朱紫斑烂。庭院环绕以树石围墙,有小桥曲经通幽,与外部湖山景观相隔离,似乎有遮挡秋之意。庭中窗明几净,一老者独坐养神,有侍童汲水煮茶,一派闲情逸趣。
冬景,画湖边四合庭院。高松挺拔,苍竹白头,远山近石,地面屋顶,都铺满积雪,显得茫茫一片,桥头一老翁骑驴张伞,前者侍者导引,似乎为了寻诗觅句,无妨踏雪寻梅,颇多闲适之趣。
刘松年 《秋窗读易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秋窗读易图》画面表现的是读书的场景。水畔树石掩映之下,书斋门窗敞开,主人在窗前展卷沉思,一书童在门外侍立。景色清幽,主人儒雅,童子恭敬,各尽其态。房屋、院落、树木、篱笆墙,都是精工细写,一丝不苟,将秋天的氛围渲染得恰到好处。一片湖光水色之外,更有远景的山石隐现。山石的画法明显是学自李唐,先用健朗的线勾轮廓,然后施以斧劈皴,精巧、有力,青绿设色,杂树用夹叶法,这些都是典型的南宋画法。但细读之下,却也不尽然。《秋窗读易图》同时呈现出另一种风貌。我们拿这张作品和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做比较,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四景山水图》画山石用斧劈皴和淡墨渲染,具有刚硬的特点。树的弯曲,用笔偏于方折,远山仅画一角。虽然画面的总体感觉上是湿润的,但具体景物却是干裂的。再看《秋窗读易图》的山石画法,很明显地具有董源、巨然的风格——长披麻皴的运用和具有江南柔美的韵致。另外,从树木、苔点、远山、秀水的画法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一种萧散和淳厚,这又具有元人的绘画风韵。
总体而言,《秋窗读易图》较之《四景山水图》,硬朗之风略逊,而优雅、闲适之气则胜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松年的作品突破了时代的风格,以典雅、秀丽的风貌预示了元代山水画的走向。虽然元代山水画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排斥南宋绘画传统,但刘松年绘制的这件作品,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元代山水画家或者说南宗山水画家将反对的对象集中在马远和夏圭上的主要原因。
刘松年 《瑶池献寿图》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瑶池献寿图》描绘了仙山楼阁的神仙世界,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做寿喜庆场面。人物的用笔细劲畅利,神态生动。画山石以刚硬的线条勾写形体,加斧劈皴,用淡墨横抹,显得浓厚的线条突出。图中的松树也较为突出,松针先以墨笔疏疏画出,再以草绿色间点、复勾。全画构图饱满而丰富,人物与树石穿插自然,充满着幽静雅趣。
刘松年 《秋林纵牧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秋林纵牧图》绘金色秋林,二位牧童放羊的情景。上端两棵大树,根深叶茂,秋景中有红叶和青红叶,画法用干笔皴擦点染,整幅画面金碧辉煌。全图笔法精工,形象生动,具有丰收喜悦之气。
刘松年 《雪山行旅图》 四川省博物馆藏
《雪山行旅图》山势苍莽,白雪皑皑,映衬秋霜红叶丛树,分外妖娆。林中房舍隐现,桥横岸渚,山重水迴,一舟泊于岸边。行旅者踏雪而行。全画用笔工细,人物面貌高古,神态刻画入微。房舍以界画笔法,工整严谨。作者巧妙地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融为一体。画面左侧下端右上署有“刘松年画”四字款。原为张大千收藏。刘松年传世作品极少,从该画可以窥见其善画山水人物的风貌。
刘松年 《青绿山水》 立轴
刘松年 《斗茶图》(部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斗茶,又称“茗战”,是宋代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普遍盛行的一种评比茶质优劣的技艺和习俗。此图中四人,二个已捧茶在手,一个正在提壶倒茶,另一个正扇炉烹茶,似是茶童。画人物用线多为铁线描,爽利细劲,以疏笔皴擦山石,鱼鳞皴示松干苍劲斑驳之态,淡墨渲染山地。画面工写兼备,细致与豪逸并存, 以高山的苍翠秀润使人物更显生动传神。
刘松年 《罗汉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刘松年 《博古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幅情景相融的画面,郁郁森森的松林之中,几个文人墨客正在鉴赏古玩。有细细端详者,有欣然所悟者,有默默揣摩者,神情不一。远处侍女正催火烹茶,表示出一种清静脱俗的闲情逸志来。作者注意线的变化和对比,衣纹描法轻松活泼,与浓墨层层渍染的松树、山石,形成刚与柔的对比,给人一种清新出尘之感。
黄公望《水阁清幽图》:不染一尘即蓬莱,返虚入浑是神境
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每每读元四家的画作,都会感受到四家所不同的绘画气度。而黄子久与倪云林无疑是给后人可叹最为强烈的两位。他二人共同构建的“黄倪模式”是明清以来文人画的最高典范,以二人为创作榜样和学习对象,成为了明清文人画中的一股潮流。此二人各有所重,其中黄公望以其独特的浑穆和神性的绘画哲学思想深受后人的推崇。
“清六家”之一的王时敏在《西庐画跋》中评黄子久道:“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浓纤淡远,各极其致,惟子久神明变化,不拘守其师法。每见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苍莽处转见娟妍;纤细而气益闳,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故学者罕窥其津涉。”我们知道,在中国绘画史上,如果一名画家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不可学”,那无疑是很高的激赏了。无独有偶,黄子久与倪云林都曾被后人认为“不可学”。
与元四家中的另外三家不同,黄公望并非有家学渊源之人,其早年也并未接触过系统的绘画训练。大概在青年时代曾见过赵孟頫绘画,兴许赵孟頫也对其指点一二了。但此后的很多年里,黄公望并没有走上“纯艺术”道路,而是选择了积极做官。这点倒是和元四家中的王蒙极为相似。而元四家中的倪云林与吴镇,则是另一种秉性:坚决不做官。但是,仕途不顺的黄公望在经历过一场牢狱之灾后,便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执着与留恋,并服膺了全真教,从此真正开始了自己长达三十年以绘画的形式对神性世界的探索与追求。
《水阁清幽图》为黄公望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其艺术成就仅次于黄公望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这幅完成于至正九年(1349年)的作品,与黄公望同时期创作完成的《九峰雪霁图》、《天池石壁图》以及基本完成的《富川山居图》共同成为了黄公望艺术巅峰的“四大名作”。此前,笔者曾写作过《富川山居图》以及《天池石壁图》,对这两幅黄子久的代表作的品读,也大致上完成了对黄公望创作理念的基本概括。《水阁清幽图》虽然在体量上无法与《富春山居图》相比,但是,就艺术表现以及思想内核上看,《水阁清幽图》与《富春山居图》可称得上是黄公望创作生涯中的两颗明珠。一卷一轴,构成了黄公望可游、可居、可望的神性世界。
黄公望《水阁清幽图》
一、《水阁清幽图》:生命的逸音黄公望《写山水诀》云:“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相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黄公望的“三远论”无疑是在北宋郭熙的“三远论”基础上的再创造,并且是极具个人特色和绘画实践的“三远论”。这幅《水阁清幽图》便是黄公望“三远论”的代表作。
画面下方画一条山间溪流,隔开两岸石木。两边的树木毓秀挺拔,其中临岸的树微微呈向对岸靠的姿态,即刻是画面在庄穆之外有了几分活泼的生趣。再看两岸树的表现,浓淡有分,错落有致,远近关系一目了然。树叶的描绘,既有浓墨皴染,也有淡漠轻擦;既有粗笔点染,也有细笔勾勒。树的形态各异,不作重复描绘。观之,并不觉得单薄,又不觉得过于阻塞。画面流动的气息如同溪流一般自由流动着。
溪流前处,几座阁屋坐落其中。被林木掩映环绕的阁屋,显得格外宁静幽闭,一派清幽气象,从此处升腾起来。黄公望的许多作品中都可见这样的阁屋,这并不是王蒙作品中一个提供世俗生活居住的空间,而是黄大痴内心中所向往和牵挂的精神隐蔽之所。阁屋的存在,不是为了呼朋引伴了在逍遥,也不是用于吟诗作画附庸风雅。若是如此,便是“邪、甜、俗、赖”了,而黄公望倡导“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
黄公望《水阁清幽图》局部1
服膺全真教之后的黄公望,始终在创作中努力寻找一个远离世俗并与神道相近的栖息之所。而这个栖息之所,正是黄公望不遗余力在画面中所描绘的阁屋。在黄公望的意识中,阁屋的存在,是介于尘世居所与神仙居所的地方。由此,我们大概可以从神性的角度来理解黄公望作品中这些独特的意象。
阁屋后面,是一大片的密林。其中近处的林木以浓墨来表现树的郁葱,而远处的则以淡墨表达一种深远之境。就此,阁屋被下方相连的土石以及上方成片的密林围绕在一个不被打扰的世界里。如果,画面就此为止,似乎就无趣了。再向上看,雾气氤氲,隔开着下方的林木、阁屋和上方的山台、山峰。但是,黄公望并没有让这种相隔来得太仓促和毫无关联。画面右边的山,已经越过了烟岚的高度,与对岸的平台以及山峰隔雾相望。左侧的一两株挺拔的树叶极力向上生长至半山的高度,同样与对岸的山峦形成呼应之势。这两株“高耸入云”的树,既形成了湖面上下前后的呼应,同时也丰富了画面左边的内容。
雾气上相连结块的平台,向后延伸至山后,塑造出了山峰的深度与层次。平台边缘的线条,清细而流畅,下方以湿笔刷出掩映在云雾中的朦胧感。山谷的深度在这种朦胧的表现中形成一种极富张力的笔墨语言。平台上的石块则以相对浓的墨色来组织画面物象,从石块往上,沿着一条山脊上行,蜿蜒盘曲之后,直入山巅。山以披麻皴表现,施加以矾头、苔点,亦真亦幻之间,构成了子久神秘的世界。
黄公望《水阁清幽图》局部2
山峰下方平台的世界,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世界。这是黄子久为仙人精心构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神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山谷下方阁屋所在的世界是两种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关联牵挂的世界。朦胧的云雾,阻隔着人间与仙境,让仙境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却又似乎有一条道路正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观平台山石,似乎可见黄子久正坐在其中。正如李日华记载:“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亦不顾。”
通观此幅《水阁清幽图》,只见笔墨精妙,虚幻相生。在有韵律的笔墨节奏中,仿佛听见了来自天国的逸音。这是黄子久心中的生命清音,亦是黄子久隐遁在神境的生命吟叹。
黄公望《水阁清幽图》局部3
二、超越现世,纵横吞吐褪去烟火气的黄子久,借纵横山水得神性。读黄子久的绘画作品,如同读一个个古朴的意象叠加的诗词作品。看不到拖泥带水,也看不到直接的情绪流露。一切秩序又都是非秩序的,一切真实,又都是虚构的。
中国绘画始终在寻找“真”,但是此“真”非形式上的真实,而是生命的真意。北宋苏轼生平爱竹,“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苏轼有一次用朱则笔画竹,旁人笑他:哪有红色的竹子?苏轼驳说:又哪里有黑色的竹子?在传统文人观念中,黑色的墨画的竹子就是真实的竹子。苏轼关注的从来不是形式,无论是黑色的竹子,还是红色的竹子,又或者是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竹子,这些形式上的色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中的颜色。苏轼的红色竹子是其心中的竹子。
黄公望所服膺的全真教,本就是寻求“真”的宗教,“全真”之意便是“去除虚妄,独全其真”。由此可见黄公望对真的信奉与追求。黄公望在《题莫月鼎像》写道:“道以为体,法以为用。金鼎玉蟾,混合空洞。风雷雨电,飞行鼓从。被褐怀玉,从事酣梦。形蝶成光,真成戏弄。噫!孰有能知师动中之静、静中之动者乎?”究竟是动中之静,还是静中之动?黄公望看得真切,他的真就是超越形式上的“动”与“静”,达到生命的真实之境。
黄公望的山水并不是形式上的真实山水,而是属于生命的“意思”山水。他在《写山水诀》中说“画不过意思而已。”这真的是有“意思”的绘画理论。我们在黄公望的众多绘画作品中感知到的是一种区别于前后世画家的神性特质,而如果要回归具体到一种理论层面,我想,“画不过意思而已”大概可以称之为大痴道人绘画的宗旨。
且不说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富春山居图》中所展现出来的纵横天地的气韵,就说其82岁时完成的一幅巨轴《铁崖图轴》,画面中所散溢出来的仙灵之气,真正的是一位老艺术家彻底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表现,而达到了与仙人共舞的高度。在这幅作品中,山峦是被云气割裂的,云气则贯穿在宇宙之中,人迹在此已经微不足道了。黄公望旨在以绘画的形式表达一种生命的意思与情趣。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黄公望的山水,不是倪云林那般的孤寂之美,也不是赵孟頫那样的复古之美,脱胎于董巨与赵孟頫的大痴道人山水,有一种独属于其个人的浑穆之美。我想,这大概和其真正从事绘画的年龄以及此前五十年的阅历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年龄上说,出狱后的黄公望已经五十岁“高龄”,此时的他很难去表达一份南宋式样的小景山水的明艳。特别是在其八十岁左右的创作成熟阶段,去作品更具岁月的风华。“去除妄念,独全其真”是彼时黄公望所致力的山水生命意思。
既然黄公望的山水不是追求形式上的真山水,那么是否是表现的山水?与过去的大师相比,黄公望的山水,既不是真山水,也不是表现山水。过去的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形成的共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即“文以载道”,表现在绘画中,特别是山水中,便是“山水载道”。虽然黄公望所服膺的宗教是“道教”,但并不是说黄公望的绘画就是“载道”的。事实上,我们在黄公望的作品中,看不到玄奥的“道”,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真性灵。这点在元四家其他几人身上均是共通的,即便是后来的徐渭、石涛、八大等人,也莫过如此。“载道”的任务并不由文人画去承担,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画之所以如此璀璨的一个重要因素。倘若,文人画是以载道的面目出现,我想,文人画的历史地位大概和院画一般,甚至不及。
既非真山水,亦非表现山水,黄公望以及其后来者们的文人画,其根本的旨趣在于呈现个人性灵。他们并非要创造一个不同的绘画题材,而是在创造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生命宇宙。在《水阁清幽图》中,黄公望的生命宇宙是两岸的林木,是溪流便的阁屋,是阁屋上方的云气,是云气上的峰峦,它们共同构成了黄公望的生命宇宙,一个超越了尘世,超越了自然形式的山水秘境。这里不是尘世之人的山水,这里也不是郭熙所言的“可游,可观,可行,可望”的山水,而是一个“可真可幻可虚可实”的性灵山水。也因此故,黄公望的山水,有一种独有的纵横吞吐的磅礴气象,山山水水,云蒸雾绕皆为其存。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三、“画仙”黄子久面对黄子久这个人,有时候我常常觉得难以置信。五十岁才正式学习绘画,到八十岁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近代的书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齐白石也是到“晚年”才正式踏入艺术的大门,并被艺术圈所接纳。而后三十年里,作画成为了其生活很大的一部分。而黄公望在那样的乱世中,在一个汉人不被接纳的时代,他以绘画来表现一个心中的神仙秘境。这需要多大的气魄,又需要多强的坚韧之心啊。
黄公望《天池石壁图》
他只画自己心中的山水,表现自己的生命思考,展现自己的生命宇宙。或繁华璀璨,或孤寂空灵,或庄穆森严,或典雅清淡。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隐居,不是王蒙式的避世,也不是后世明清文人山水中只是为隐而隐。黄公望的隐,是神隐。与神仙同居,与神仙对话,与神仙交游。如果画史也能像文学诗词史那般有“诗仙”、“诗圣”、“诗鬼”等说法,我想,黄公望大抵上可以说是“画仙”了。在他的作品中,笔笔墨墨尽是仙气萦绕。
绘画是一种图像式的语言,有的时候,绘画比起诗歌,更富有延展性与可读性。艺术家本人只是展现给你一幅图像,而其中的情趣,需要看画的人自个儿去品味。但是黄公望却很高明地借助无声的图像式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份浪漫的情趣,一份不为世俗所累的神境。在这里,艺术家就是这唯一的生命源泉。
从唐到元,跨越五代十国与南北宋,“诗仙”李白与“画仙”黄子久达成了某种神秘的呼应。他们的人生轨迹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渴望仕途,却终究被官场抛弃,最终,一个在诗中寻得神境,一个在画中觅得蓬莱。
黄公望《仙山图》
四、品画澄心我常常对自己说,读画读的非笔墨,而是人生与生命情趣。这份情趣,无所谓好的坏的,无所谓热情的与平淡的,亦无所谓雄浑的与淡雅的。每一份生命情趣都值得我们去珍视,也值得我们去守护经营。善待之,便是情趣;漠视之,则是无趣。我大概不想做一个无趣的人。
生命终究不是一条涓涓细流的溪水,两岸的风景也断不是只有“万紫千红”。生命的宇宙里,既有繁星璀璨,亦有电闪雷鸣;既是宁静悠远,又是暗潮涌动;看得见朝花夕拾,也听得到哀鸣不绝。面对这些变幻的宇宙,我们常常无所适从。但是,子久却给了我们答案:寻觅自己的生命宇宙,不为形式所累。
黄公望的神境绝不是彻底的远离世俗生活,而是当下即蓬莱,或者说,以超越的生命之眼,观当下的生命体验。此也即黄公望的无分别境界。黄公望有《题自画雨岩仙观图》诗:“积雨紫山深,楼阁结沉阴。道书摊未读,坐看鸟争林。”寥寥二十个字,道尽了“即尘世即蓬莱”的生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