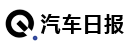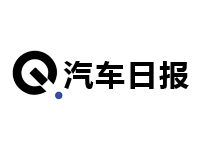又一新材料项目落户仪征马集镇
6月13日下午,仪征马集镇与江苏特博特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签约,特博特新型材料项目正式落户马集。仪征市副市长田文远,市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马集镇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一办八局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田文远代表仪征市委、市政府对项目签约表示祝贺,他表示,合作双方要以今天的签约为新的起点,精诚合作,携手并进,共同落实好协议的各项内容。他强调,马集镇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为项目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着力为企业营造最优越的营商环境。他指出,投资方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在项目建设中加强沟通交流,加快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成运营。
马集镇党委书记朱载鹏为活动致辞,他表示,马集镇将以签约活动为新起点,加强与项目方沟通交流,实施项目全过程帮办代办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矛盾难题,迅速启动项目服务各环节工作,切实以优质服务推动项目早日开工、早日投产、早日见效,努力为项目推进提供一切便利,尽快推动特博特项目成为支撑马集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项目方负责人、江苏特博特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坤致辞。他对仪征市和马集镇两级政府的高效服务标识衷心感谢。他表示,江苏特博特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性能优越,市场前景广阔,企业将用好产品和技术优势,继续加大产业研发,拓宽和丰富产品类型,千方百计地把企业培植好,经营好,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马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先秋与周成坤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
马集镇党委副书记张文杰主持签约仪式,他表示,马集镇将以本次签约仪式作为全新起点,进一步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全力提供项目发展所需的要素保障,为企业开工投产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切实做实项目服务文章。
特博特新型材料项目位于马集镇工业集中区天瑞路北侧,由江苏特博特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5亿元,一期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40亩,固定资产投资10000万元,设备投资5000万元;主要从事蒸汽加压混凝土(ALC)板材及装配式部件集成化产品生产、销售。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30万立方板材,年开票20000万元,税收2500万元。
来源 瑞映马集
韩高年:武威“王杖”简册的文本性质与文体功能
摘要:武威发现的与汉代“高年授王杖”制度有关的简册有三个,一是1959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二是1981年征集所得之“王杖诏书令册”,三是1989年旱滩坡汉墓出土之“王杖简册”。以往研究者多将此类文本界定为抄撮律令而成之“挈令”。考虑到三个王杖简册均出自墓葬,且与标志身份的“鸠杖”一同随葬等细节,以及“王杖十简”文本中提及墓主人幼伯的死亡时间等信息,有理由认为,此类简册应为配合丧礼而写作的“丧葬文书”。其文体功能则是一方面显示墓主人身份,另一方面也借用人间律令的权威昭告“地下”,以保证墓主人的特权不受到挑战。1959年的秋天,在河西走廊中段武威市以南15公里祁连山脚下杂木河西岸的台地上,考古人员发掘了磨咀子汉代墓葬群中的18号墓,其中出土了著名的“王杖十简”。这组木简共有10枚,简长约23—24厘米,据整理者言,“其内容主要是建始二年和‘本二年’,关于高年授王杖的诏令,史学界称其为‘王杖十简’。”关于“王杖十简”的排序、释读、抄写年代,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汉代养老制度等问题,学界的讨论相对比较充分,但对其书写背景、文本性质、文体功能及文章学价值等问题,则仍未能达乎一间。尤其是在1981年“王杖诏书令册”面世,1989年武威旱滩坡汉墓“王杖简册”出土之后,将这三个简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很不够。
笔者认为,对“王杖十简”等三个相关简册文本性质和文体功能的讨论,应当结合墓葬出土的简册以外的其他随葬品,以及由其中所显示的汉代河西地区丧葬礼仪等信息,予以综合考察。笔者认为,“王杖十简”属巫祝为死者所作,其文体功能也非人间诏令,而是与墓中所出鸠杖一道,向地下世界确认墓主人“受王杖”者应该享有的特权。今呈鄙见,求正于方家。
一
为讨论之方便,先据党寿山先生所释,以及郝树声等学者所校订成果,引述“王杖十简”原文于下:
[1] 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勝(朕)甚哀老小。高年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
[2] 比于节,有敢妄骂詈殴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郞(节)第,行驰道旁道。市卖,复毋所与。
[3] 如山东复,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明在兰台石室之中。王杖不鲜明
[4] 得更缮治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英页部游徼吴赏,使从者
[5] 殴击先,用(因)诉地太守上谳廷尉,报:罪名
[6] 明白,赏当弃市。
[7] 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
[8] 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
[9] 兰台令第卅(卌)三,御史令第卌三,尚书令灭受在金。
[10]孝平皇帝元始五年幼伯生,永平十五年受 王杖。
上引第10简,《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排列为第九简,并认为是单简。研究者指出简文记录“灭”的官历,“灭受在金”似指受杖,“在金”之“金”当是地名,或疑是金城(郡)之“金”。这些解释皆极富想象力,但尚无法完全坐实。
在“王杖十简”出土之后的1981年,甘肃省博物馆的专家又从原武威新华公社缠山村村民袁德礼处征集到一份与“王杖十简”相关的由26枚木简组成的简册(缺第15简,实际应有27简)。因其内容与“王杖十简”相似,且该简册之首简言“制诏御史……”,末简有“右王杖诏书令,在兰台第卌三”字样,故学者们称之为“王杖诏书令册”。“王杖诏书令册”简背有简序编码,只缺第15简,相对比较完整。为论述之便,兹引据释文如下:
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杀伤人,毋告劾也,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第一(简背,下同)
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復,復第二
人有养谨者扶持,明著令,兰台令第卌二第三
●孤、独、盲、珠孺,不属律人,吏毋得擅徵召,狱讼毋得(□)。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第四
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与归义同,沽酒醪列肆。尚书令第五
臣咸再拜受诏建始元年九月甲辰下。第六
●汝南太守谳廷尉,吏有殴辱受王杖主者,罪名明白。
制曰:谳何,应论弃市,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坐殴抴受王杖主,使治道,男子王汤 第八
告之,即弃市。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第九
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第十
得出入官府节第,行驰道中,列肆贾市毋租,比山东復。第十一
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第十二
皇帝陛下:臣广知陛下神零,复蓋万民,哀怜老小,受王杖、承诏。臣广未第十三
常有罪耐司寇以上。广对乡吏趣未辨,广对质,衣疆吏前。乡吏第十四(第十五简缺)
下,不敬重父母所致也,郡国易然。臣广愿归王杖,没入为官奴。第十六
臣广昧死再拜以闻第十七
皇帝陛下。第十八
制曰:问何乡吏,论弃市,毋须时;广受王杖如故。第十九
元延三年正月壬申下第廿
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第廿一
弃市。令在兰台第卌三。第廿二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坐桀黠、击鸠杖主,折伤其杖,弃市。南郡亭长第廿三
司马护,坐擅召鸠杖主,击留,弃市。长安东乡啬夫田宣,坐□第廿四
鸠杖主,男子金里告之,弃市。陇西男子张汤,坐桀黠、殴击王杖主,折伤第廿五
其杖,弃市。亭长二人,乡啬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殴辱王杖功,弃市。第廿六
■右王杖诏书令在兰台第卌三第廿七
“王杖诏书令册”是征集所得,有的学者因其不是出自考古发掘而怀疑其真实性,但被后来者所驳正。以上所引根据党寿山先生的释文。党先生认为:“新出王杖诏令册,内容共分三部分,包括五个诏书令文件。第一简至第六简为第一部分,包括两个诏令:第一简至第三简,是尊敬长老、抚恤鳏寡的诏令,称‘兰台令卌二’;第四简至第六简是抚恤孤独、废疾的诏令,为成帝建始元(二)年九月甲辰发布的诏书。第七简至第廿六简为第二部分,其中包含三个诏令:第七简至第十一简,是高年赐王杖的诏令;第十二简至第廿简,是处决乡吏殴辱王杖主的诏书;第廿一简至第廿六简,是年七十杖王杖的诏令。同‘王杖十简’建始二年九月诏。”据此,党寿山先生的“王杖十简”释文及简序排列参照“王杖诏书令册”次序,认为“王杖十简”中的“《本始令》在前,《建始令》次之,再次为篇目简,最后是幼伯受王杖记事”。其说比较符合实际,可以信从。
关于“王杖十简”的文本性质,最初的释读者认为是诏书。其理由是“10简共记三人受杖,即先(河平元年犹存)、幼伯(永平十五年犹存)及灭。此三人当是一家,故将有关受杖的简书附系于杖头入葬”,并言简文中“既有诏书,又有记事”。郭沫若说:“《王杖十简》上的两项诏书,据我看来,都是西汉成帝时下的。”认为“王杖十简”是诏令。就其内容而言,这样说也符合实际,但为什么这些诏令会被以特定的形式和目的编辑在一起,仍然是一个问题。
1981年“王杖诏书令册”出,学者们大多仍认为“王杖十简”的文本性质是“诏令”。日本学者大庭脩最初认为“王杖十简”是决事比,即司法判决的案例,但此后又因“王杖诏书令册”的出现而改变了最初的看法。籾山明则认为:“王杖十简及王杖诏书册的整体,就是在汉代被称为挈令的法规实例。……挈令的本质,不在于‘挑选’‘编集’这一编撰程序,而在于‘悬挂’‘揭示’这一公布形态。如果着眼于颁布、揭示这个侧面,较之令典、令书,它更接近于通告、悬札之类。”
以上各类关于“王杖十简”文本性质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却都围绕着诏令或是其传播形式立论。然而,夷考其实,如果承认“王杖十简”属于墓主的随葬品这一事实,则以为其为“诏令”或“挈令”的说法,显然是无法回答这些诏令为何被编辑为现有的文本这一根本的问题。
二
笔者认为,从这份文书的文体功能层面来看,上文所引“王杖十简”的文本,由行文意义逻辑完足的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1-8简,包含有两条诏令和一个案例。第一条诏令从“制诏丞相御史”至“明在兰台石室之中”,就是整理者所谓的“本始令”;一个案例,从“王杖不鲜明”至“赏当弃市”,记叙了“王杖不鲜明可以重新制作或修缮”的规定,以及游徼吴赏因为纵容随从殴打名叫“先”的王杖持有者而被判弃市的案例;第二条诏令从“制诏御史曰”至“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其内容是叙述受王杖者的年龄、待遇、持有的法律豁免权等,即整理者所谓的“建始令”。
第二部分:第9简,记载诏令“篇目编次及受诏人和收藏者”。
第三部分:第10简,记叙“幼伯受王杖事”。这支简虽然简短,但却是理解“王杖十简”文本全篇性质的关键。
从内在逻辑上来看,上述“王杖十简”文本的第一部分由撮抄律令而成,几个律令和诏书之间有明显的衔接痕迹。第二部分言其篇目编次和收藏者,则是为了增加第一部分的权威性,使之自然地过渡到第三部分,落实到墓主“幼伯”的身上。这样一份带有镶嵌性质的文书,既然不是诏令,也不是诏令的汇编,那么它是什么?是写给谁看的?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王杖十简”是一种借助王朝律条诏令的权威以表达墓主生前尊荣的特别文书,它针对的阅读者,与其说是生者,不如说是死后世界的鬼神。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王杖十简”的文本当为死者辞世后,其亲属委托地方上熟悉丧葬礼仪和朝廷律令的人,抄撮旧有律令诏条而成,其目的是希望死者能在死人的世界里享有与活着时一样的特权和尊荣。这从简文中一些特别的用语可以看出端倪,简文中的“明在兰台石室之中”“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以及记述诏令编次的用语,显然都不是诏令本身的内容,而是文书的制作者刻意强调诏令的权威性的。“明在兰台石室之中”意谓“优待高年的诏令藏于兰台石室之中”,暗含其权威不可动摇的意思;“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则是通过具体讲明殴打和辱骂持有王杖的“先”的吴赏及其从者被弃市的案例,起到警告和震慑作用。至于注明诏令编号及典藏处所的用语“兰台令第卅(卌)三,御史令第卌三,尚书令灭受在金”,则是为了进一步申明王杖持有者所应有的政治待遇、享有的特权以及法律上的豁免权的法律依据,表明其不可动摇性。
日本学者大庭脩曾指出:
我读“王杖诏书令”册,感到最有兴趣的是第3简的“明著令,兰台令第卌二”,即所谓著令用语。这意味着带有“明著令”著令用语的该诏已成为兰台令。中田熏博士曾提出假说,认为只有带着“著令用语”的诏,方能在颁诏皇帝死后编入令甲、令乙等干支令中。
大庭脩所引中田熏的观点,很能说明“王杖十简”中不属于诏令本身的表示编号和归档地点等信息用语的性质,即所谓“著令用语”。简册中的“著令用语”正表明,其中的诏令和案例,决不是“正在进行时”,而是早已颁行和编入朝廷有关机构令典的法律文献。换句话说,“王杖十简”中嵌入诏令和案例(“决事比”),其目的并非为“汇总”或“编辑”,而是另有考虑。大庭脩先生认为:“在对年届七旬的老人授予鸠头王杖的同时,也给予这些文书。其中所书的令文与判例,就是他们的特权证明,也可以说是保证书。不过在这些文书中书写了怎样的诏书与令,恐怕会因当时的承办官吏而有所不同。‘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的出现,正反映了这一点。”除去认为“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是墓主生前被授予王杖时同时颁发这一点,大庭氏对这类文书性质的判断又向事实逼进了一步。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王杖十简”的制作者抄录两诏令和一个案例的目的,正在于引出第三部分,也即上引第10简“幼伯受王杖事”,告诫地下世界不得无端骂詈及征召持有鸠杖的幼伯,并保有其皇家赋予的种种特权和法律上的豁免权。
陈直先生认为:“磨咀子十八号墓主人,应为幼伯,受王杖者,亦仅幼伯一人。随葬时重钞录两旧诏令,以为受王杖者之尊荣,其荣身与幼伯有关,其事实与幼伯无涉。两汉人对于诏令有需要时,可以查明重钞,例如居延全部木简,是西汉中晚期之物,有‘前三年十二月辛巳凡九十一字’、‘孝文皇帝五年’、“孝文皇帝三年十月庚辰下凡六十六字’,各诏令之记载(见居延汉简释文(重庆版)卷四,二〇页)。本简第一至第九所重写建始二年及河平二年两诏令,亦同此例。考古所编辑室解为先、灭、幼伯三人先后皆受王杖,年代固属相去太远,前后亦不伦类,因而分前八简为西汉河平时物,后二简为东汉永平时物,其说殊属失之牵强。”陈直先生指出此非原始诏令,是为表示“受王杖者”(死者)“尊荣”而“重钞录两旧诏令”;并解释“尚书令灭受在金”之“金”为“金布令”,即关于府库钱财的令,因为要赐予受王杖者以布帛,即在金布令中加以规定。这些看法,可谓慧眼独具。然而所谓“重钞”,并非照搬原文,而是按照当时的丧葬习俗,通过抄录诏令,有意重组一种新的文本。胡平生先生认为,“王杖十简”“为‘王杖诏书令’之摘抄”,而不是诏书令本身,这为我们确定其文本属性和功能指明了方向。
“王杖十简”属于告示地下世界的文书,还可以从其与标示死者身份的鸠杖的关系上得以印证。“王杖十简”出土于磨咀子汉墓18号,据考古发掘报告称,出土之时几片简还缠在同为墓中所出鸠杖上。从残片上观察,当初10枚简都是系在鸠杖上端的。鸠杖表面光滑,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死后随葬。
另外,1989年考古人员在武威柏树乡旱滩坡发掘的一座汉代墓葬中,也发现了与“王杖十简”相同的木简。据考古发掘报告称,“随葬品置于墓室前部的左右两侧,未扰动。木简1束,置于棺盖上面。鸠杖1件,置于棺的前部,壶、罐、仓、灶、井、盘、豆等陶器,置于棺首两侧。铜镜及五铢钱、货泉等出自棺内墓主骨骸之下。”“简1,长20、宽1厘米,下端略残。简文30字:‘制诏御史奏年七十以上比吏六百石出入官府不趋毋二尺告刻(劾)吏擅徵如(侵辱)’。简11,长14、宽1.1厘米,下残。简文19字:‘长安乡啬夫田顺坐徵召金里老人荣长骂詈殴□’……”很显然,此墓出土之简册,与磨咀子18号墓出土之“王杖十简”一样,也是与鸠杖配合,发往死者世界的特殊“文书”。日本学者富谷至对“王杖十简”文本性质的判定虽然不无可商之处,但他认为其功能是将墓主的身份“通知地下世界”,以“希望继续保持墓主待遇与特权”,则堪称卓见。
三
磨咀子汉墓中以简册随葬的,还有第6号墓。陈梦家先生认为:“第六号墓出现了如此大量简册,故对于墓主人为谁,值得推测。简册中和其它遗物中未留有名姓,故无法知其为何人。墓制和随葬物品均属中常,且以《礼》书随葬,故推想其人不属于上层统治阶级,而属于当时的官吏或士人阶层。汉世以简写经书随葬者,惟见东汉和帝时的周磐。据《后汉书·周磐传》,磐少学古文《尚书》,尝三为县令,以母丧‘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临终遗令写《尧典》一篇同葬。周磐以治《尚书》的经学儒师,遗命以所学之《尧典》置棺前,此事与第六号墓有可相印证之处。治《尚书》的老儒周磐以《尧典》篇随葬于其墓中,则第六号墓主人以《仪礼》九篇随葬,或系教授《仪礼》的经师。此所殉者,应即是墓主生平教授的专经。所不同于周磐者,此人不以专为殉葬而写的所专之经随葬,而以平日诵习的简册(由于甲本有学者钩画的记号)随葬;不但以《仪礼》的简册随葬,而且以不同的三本《丧服》随葬。”由此可知,汉代文人或士吏有专书简册以随葬之习俗,有时则变通为以生前所用之简册随葬。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简策向地下的世界昭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和荣耀。
据发掘报告,磨咀子6号墓中所出十一支日忌和杂占类木简第一简之背面,书写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这大概是记录在墓主人(文学)辞世后,其弟子賵赠“谷五千斛”为墓主人举办丧礼的情况。在尹湾汉墓随葬的竹简中,除了标明其身份的集簿、东海郡吏员簿、历谱、名谒、衣物疏等外,也有记录亲朋故旧向死者家赠送赙钱数量的简册。这种情形也见于汉魏时代的墓碑中。如《马姜墓志(永平七年九月十日)》末尾言:“皇上闵悼,两宫赙赠,赐秘器,以礼殡。以九月十日葬于芒门旧茔。(下残)子孙惧不能章明,故刻石纪□。”《□通封记》于碑记末言:“□为父作封□□□度博望□□时工宪工□,功夫费凡并直」□万七千。二月卅日毕成。”这是记录赙赠和丧葬费用的例证。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指出汉代丧礼中赙礼的具体情形:
向丧家送礼是吊唁者必须遵行的行为规范,礼物称“賵礼”或“赗钱”,包括钱财和实物。这两种物品既包含对丧者家庭的精神慰问,更带有支援丧葬活动和丧家日后生活的实际意义。据《论衡·量知篇》“贫人与富人均赉钱百,并为赙礼”的描述,普通百姓的赙钱可能在百钱左右。江苏仪征西汉墓木牍记录死者之弟从邻近地区获取的亲友赙赠钱物有钱、银、缣、布、履和绣衣,“凡值钱五万七钱”(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这是汉代赙赠状况的实际说明。
由以上所述推断,磨咀子6号墓中“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应当是指文学弟子向老师(死者)家属赠送的“赙礼”。而墓中的《仪礼》简、日书,以及其他木简,则是显示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随葬品。美国学者伊沛霞认为:“与其他随葬品一样,墓志铭的功用是帮助墓主从今生过渡到死亡世界,保证他/她有冥界的安康,并向冥界通报他/她的身份地位。……墓志铭也起着保障墓主不受到各种危害以及确立其尸骨及灵魂之墓地拥有权的作用。”同理,上文所讨论的汉代墓葬中的简册文书,应该也具有墓志铭的功能。
除“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外,类似内容的简册在武威还有发现。1989年8月,甘肃省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武威柏树乡下五畦大队旱滩坡汉墓清理发掘时,发现残简17枚。经过清理现存木简16枚。木简均系松木质。木简下端略残,有的下端残缺1-3字,简长一般为21厘米左右,宽约1-1.1厘米。木简呈淡黄色,简文单行墨书隶体,字迹清楚。每简11-28字不等。墓葬整理者依据墓葬器物形制、组合以及简文所见“建武十九年”年号,推断该墓葬年代约在东汉中晚期。发掘者指出简文内容分两类:一类仅2枚,为高年养老授王杖的诏书;一类14枚,为涉及保护农时、社会治安、户籍、田地等内容的各种律令条文。也就是说,这一简策节选集合了各类律令。李均明先生分析了墓中所出简册的内容后认为,这就是“挈令”,“挈令的实质当为中央有关机构根据需要从国家法令中提起与自己有关的部分,以地域命名的挈令则是根据地域需要提起。”《广雅·释诂》:“挈,犹提也。”李先生的判断对了解什么是“挈令”有重要价值,对我们讨论旱滩坡汉墓所出简策的组成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这个简册出土于河西走廊的武威,墓主人也不是什么达官显宦,所以无论如何都不是“中央有关机构”所为。因其亦未冠以有地域特色的命名,应当也不是地域性的“挈令”。
笔者认为,要确定这一以高年授王杖诏令领起的集合各类律令的简策的文本性质,还要考虑到此简册在墓中与鸠杖同置于棺木之上这一事实。据考古报告称,这一束木简,置于棺盖上面。鸠杖1件,置于棺的前部。陶制生活用具置于棺首的两侧。铜镜及五铢钱、货泉等在棺内墓主身下。出土时简册编绳痕迹清楚,两道编绳缀联。结合磨咀子18号汉墓的发掘情况,我们很难说简册和鸠杖不是与其他随葬品一起为保障墓主人在死亡世界里的身份和安全而人为设置的一种特殊的仪式语境。而此简册中,简1:“制诏御史:奏年七十以上,比吏六百石,出入官府不趋,毋二尺告刻(劾),吏擅征召”,简11:“长安乡啬夫田顺坐征召金里老人荣长,骂詈殴”,从简文内容看,与“王杖十简”第1、4简,以及“王杖诏书令册”第4、10简部分内容相关,当归王杖诏书类。
和“王杖十简”一样,“旱滩坡汉墓简册”也应该是为墓主人的葬礼而精心结撰的文书,其结撰方式借鉴了“挈令”的写法,但却不是挈令。所不同者,旱滩坡所出简册还涉及到“农时”“户籍”“蚕桑”“禁盗”“罪不得赦”“夺户”“灾害应急”“泄露司法文书”“度田不实”等内容。第16简云:“建武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己亥下”,案“建武”为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十九年当为公元前43年。李均明先生据汉简文书签署常例所言,此简既是此简册书写下发之时间,同时作为丧葬礼仪文书,也是墓主人下葬的具体时间。
四
此外,从近年出土的汉代墓葬文书来看,以书籍随葬,或抄录官府诏令律条,借用律令的格式和术语,以针对地下的世界,保证墓主在死后享有尊荣的做法,多见于汉晋墓葬出土“告地策”“镇墓文”“买地券”“符箓”等简册。这类文本中多用“敢言之”“移”“急急如律令”“如律令”等公文书或法律文书的术语。英国学者鲁惟一指出:“将一部文献葬入墓中,大概是想用来代表死者的财富。有了这些文献,他就能够凭借自己的职业成就给地府留下印象,从而巩固待遇方面相应的特权。”这种说法大体符合实际,表明这种情况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丧葬礼俗。
告地策通常写在木牍上,并且有封检,其行文格式略同于汉简中常见的过所文书“传”,主要记录日期,死者姓名、籍贯、携带财物及告知对象。告地策和遣策衣物疏等共同使用,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则是湖北荆州高台18号汉墓所出,该告地策置于遣策之前,其文云:
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亭手,产手。
这是名叫“起”的中乡长官替墓主人新安“大女燕”向江陵丞提出迁徙的申请,准许其由江陵迁往安都,该申请获得江陵丞龙氏的批准。《列子·天瑞》载:“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可知在古人观念中,人死为归乡。上引文书,大概是因为死者不愿客死他乡,想在死后返归故里,因此仿人间律令撰此“告地策”。据汉制,平民若出行,需按例“自言”(自我介绍)提出申请,由县丞或与县丞相当的官吏批办,因此文中写明“徙安都”乃大女燕“自言”,即自愿迁徙,同时写明与之同行的还有大奴甲、乙和大婢妨以及时间和地点。“名数”在这里就是指户籍(或名籍),名籍要填写户主与同住家属佣人名字,以及奴婢与应报之财产数。这则“告地策”在形式上用的完全是地上官方“过所文书”的行文格式。和“王杖十简”一样,正是借官府文书以告知地下世界的典型案例。
为比较和明确二者的关系,我们不妨举一篇过所文书的例证如下:
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守令史翊、佐褒。七月丁亥出。
这则因派遣亭长王丰外出到酒泉、敦煌、张掖购置马匹的过所文书,其中除说明持有者身份外,还提示沿途驿站给予食宿方面的便利。“从者如律令”表明其公务文书的权威性。末有签发官员的具名。该“传”出自《居延汉简》170.3A。上举“告地策”的格式与出自《居延汉简》的这类名为“传”的文书十分相似。“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即“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亭手,产手”则是具体办理者的签发,与上引“传”中的末二句正同。
镇墓文一般书写在镇墓瓶上,朱砂书写,用以阻隔地上和地下世界,防止死者作祟,解除殃咎。河西走廊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有130余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时代比较早的如陕西西安南李王村汉墓所出东汉初平四年(192)的王氏镇墓文:
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直危。天地使者,谨为王氏之冢,后死黄母,当归旧阅。慈告丘丞墓柏地下二千石,蒿里君墓。黄墓主墓,故夫人决曹尚书令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隐如故。今后曾财益口,千秋万岁,无有央咎。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冢门。地下死籍消除,文他央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震郭门,如律令。
这篇镇墓文虽然以“天帝使者”的语气“告”地下“丘丞”“墓伯”及“先人”等神鬼生死异路,勿殃及生者,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但却完全是人间公文的语气,结尾的“如律令”一语表现得尤其突出。饶宗颐先生尝言:“为死者解适,为生者除殃,西陲亦流行此俗,殆古代解除术之遗。”(“饶序”)姜伯勤等学者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出土镇墓文有专门辑录研究,可参看。
其实,“王杖十简”以及上述各种汉代墓葬文书所反映的以抄录律令并借助其权威性向死者的世界表明死者尊荣和特权的习俗,根源于对于文字和律令神圣性的崇拜心理,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在研究商代甲骨卜辞和商周青铜器铭文时指出:“但有一点事实并非出于流传史的偶然,即早期中国人只把他们最贵重的材质用于与占卜、祖先崇拜等宗教实践密切相关的书写。”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简牍的书写。
综上所述,出土于磨咀子18号墓的“王杖十简”和“旱滩坡汉墓简册”,其文本性质与“告地策”“镇墓文”“遣册”等随葬文书一样,都是借用朝廷诏制和律令的形式,向地下世界表明死者的身份地位,并起着保有和维护死者在地下世界享有人间“受王杖”者的尊荣和特权的文体功能。考虑到汉晋时代河西地区的丧葬礼俗,同出于武威汉代墓葬的“王杖简册”,没有类似“王杖十简”末尾表明墓主身份的部分,而所述诏令内容却与“王杖十简”有共同之处,因而推断“王杖简册”也应当为该地区操持丧葬礼俗文书写作的民间带有“巫祝”身份色彩的礼仪操持者的“写作参考手册”。《周礼·春官》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周代专为王室服务之祝官,至秦汉而流落民间。正因为如此,这些“巫祝”才既熟悉丧葬礼仪文书的写作,也熟悉朝廷的诏书律令。在书写能力尚不普及的两汉时代,拥有了知识,就占据了权威,这些巫祝们无疑仍然是地方上的文化和宗教权威。
本文原刊于2022年第6期·百廿校庆专刊